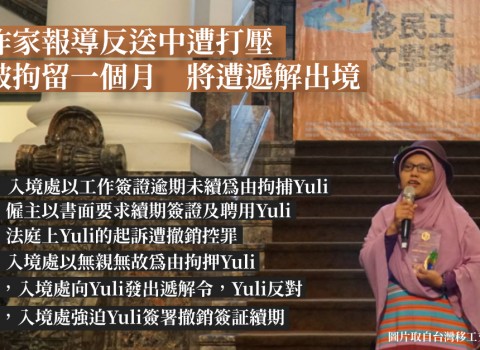本文由「公庫」合作伙伴惟工新聞提供
【惟工新聞】最近我收到一段題為「We Too」的YouTube片集(注一)。片中人闖入倫敦小矽谷(Silicon Roundabout)一棟正在興建中的34層大樓,並在頂層扎營。在裡面安睡一夜後,這名闖入者打開帳幕,看到非常壯觀的城市景色。這預示了大樓將來的住客每日都可享受這個景象;雖然更有可能的是,大樓的單位將被國際投資者買下,空置數年,然後再被賣出。到了那個時候,景觀就會成為推銷的賣點。
不久之後,我從廣告網站Craiglist看到另一則訊息。這名闖入者刊登了一個廣告,宣傳一間「人人都租得起的豪華閣樓」。廣告附有一張相片,展示他那個能夠俯瞰全城的帳幕。「我們也住在閣樓」。廣告的措辭幽默地帶出對新自由主義城市的質問——這是為誰人而建的?
公共與私人:兩種空間有何分別?
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寫道:「建造及再造我們的城市及我們自身的自由,是其中一個最寶貴卻罪被忽略的人權。」幾代的都市理論家,由芒福德(Lewis Mumford)到雅各布斯(Jane Jacobs)到瑪西(Doreen Massey),均指出城市透過公共而非私有領域得到再造。可是目前有一個嚴重問題: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包括看似公共但其實是私人擁有的露天廣場、花園、公園等不斷增加。在這些地方,我們使用空間的權利被嚴重壓縮。這些空間的擴張會對我們帶來各種影響,由個人心態到反抗的能力。
讓我舉兩個例子說明。我來自洛杉磯,最近曾經回去一趟。當我問一個老朋友市內哪裡有公共空間時,他的反應是「啥?你想買?」聽起來很諷刺,但洛杉磯正正是以取消公共空間和公共交通知名。這位朋友後來澄清,他不是在開玩笑,而是真的被混淆了。他寄了一篇來自洛杉磯時報的文章給我,文章提到洛杉磯市開始在私人市場出售行人道,為企業家增加可用來賣廣告的空間!(注二)
這就是城市的一種模式。以下是另一個例子。幾年前我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時候,我請一位同事帶我去一個景色優美的地方。然後他帶我去莫里凡(Vann Molyvann)設計的國家體育館。那是一座粗曠達建築,為舉辦1963年東南亞運動會而興建。
我們抵達運動場時,這個地方擠滿了成千上萬的人。 在這些人當中,有的在進行體育練習,有的人推著小販車售賣燒粟米,有人在掛衣服,也有無數的途人在走來走去。我甚至遇到一個在水桶洗澡的小孩。在整個空間裡,包括室內和室外,沒有任何上鎖的地方。這個混亂的地方有一股強大的能量,好像任何事都可以在這裡發生。
然後我就意識到,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缺乏這種能量。那些場所令人感到被監視,被控制,以致社群的活動難以發生,人們無法用不同方式使用這些空間。倫敦以及很多其他城市同樣有這個問題。
空間私有化 政府無力控制
在2012年,《衛報》發起一個活動,透過讀者參與蒐集英國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的分佈(注三)。這個計劃雖然未能完成,但都顯示了一個明確的趨勢。毫不出奇地,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自1980年代開始出現,其後數量與面積都不斷增加。當中包括More London,一個在泰晤士河南岸,面積達13畝的大型發展計劃。它在2003年落成,在2013年以17億英鎊(約200億港元)賣給聖馬田(St Martins),一間科威特地產公司,是英國史上最大宗的商業地產成交個案。
在這個過程中,市政廳外面的所有空間都被轉化成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意味著市民不能再市政府或大倫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總部外抗議。事實上,不要說遊行示威,就連拍攝也被禁止!去年當我在那裡與第四頻道拍攝節目時,我們很快被趕出去。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在2010年,綠黨的鍾斯(Jenny Jones)在倫敦議會(London Assembly)規劃與房屋委員會發言指出,他們花了8年時間與More London交涉,才能在自己的大樓外接受記者採訪(編按:倫敦議會設在市政廳)。
在各方大力反對的同時,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正在倫敦各處加快出現。這些發展計劃與市政府增加真正公共空間的目標矛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事實上倫敦市政府已經對城市發展失去控制。
全天候監視 扼殺可能性
那麼,我們期望怎樣的事情在公共空間發生?地理學家阿明(Ash Amin)在2008年寫道:「公共空間,指的是人群不被束縛地流動,從各種可能性中產生新的節奏。」我在金邊的國家體育館感受到這樣的元素。若空間一旦被控制,尤其是當它的公共性定義模糊,令人不清楚哪些才是合法或可接受的行為時,我們傾向監督自己的行為,限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特別是當與保安員理論的時候。
這樣與保安員接觸,會令你變得小心謹慎,進而限制自己的行為,以避免與他們發生衝突。「隸屬於這個可見領域並且意識到這一點的人承擔起實施權力壓制的責任。他使這種壓制自動地施加於自己身上。他在權力關系中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從而把這種權力關系銘刻在自己身上。他成為征服自己的本原。」傅柯(Michel Foucalt)如此描述這種自我監控的心理。
地理學家米歇爾(Don Mitchell)提出,在一個被嚴密監控的城市中,公共空間猶如一些自由的孤島,被傅柯所說的「監獄列島」包圍着。那麼,當這些空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事?社會學家桑內德(Richard Sennett)提到,私人擁有的公共空間是死的。因為公共空間應有的自發性、偶然性、混亂及節慶氣氛在這裡都被破壞了。這些空間是死的,不是因為它們不令人感到舒適,而是因為當中扼殺了各種的潛能。
「透過在公眾場所奪取空間,透過創造公共空間,群體本身就變成公共。」米歇爾寫道。「比如說,只有在公共空間,無家者能夠作為『公共』的一部分。」而我們很容易想像格蘭尼廣傳的保安會怎樣對待無家者。
企業擁有的權力不限於禁止若干種類的活動,更能阻止公眾進入這些空間——這一點在有關佔領行動的訴訟當中得到確認。在2011年10月14日,「防止『不知名人士』進入、逗留或闖入」的強制令被通過。雖然佔領行動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但這些訴訟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成為禁止在露天私人空間示威的案例。
直接行動 發掘公共空間潛能
最近,我在南安普敦大學一個有關倫敦公共空間的活動中提出,現在是時候仿效1932年由步行者協會(Rambler’s Association)發起的集體闖入行動(注四),採取直接行動避免公共空間消失。發起找出和使用公共空間的行動,著眼點不在我們已經失去的地方,而是探討我們以後能夠做什麼。
去年,當我與友人在泰晤士徑(Thames Path)漫步時,我們發現沿途有很多沒有被使用的空間,當中包括一棟需要身份證明才可進入的樓宇。有敵意的建築令人為之卻步,用差劣的指示誤導他們。我建議我們應該系統性地找出這些公共空間,並多些使用,否則我們會失去它們。
這就是我的計劃。我會嘗試用一系列的文章探討有關公共空間的核心問題:它們在哪裡?它們有什麼價值?我亦有興趣了解一些人,透過未經批准的「公共」行為挑戰私人空間,創造「短暫的自治區」(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s)的嘗試。在大樓頂層扎營,正是一個絕佳例子。
作為一名民族誌學者,我會從最底層開展這個計劃,找出各種小行動,並促成公共空間中的活動。對我來說,被看見是最基礎的問題。若有關公共空間的資訊(它在哪裡、我們可以在當中做什麼)不清不楚,眾多的小行動就能發掘各種可能性,然後我們可以有系統地記錄下來。
文章來源:
Guardian: The privatisation of cities’ public spaces is escalating. It is time to take a stand
注釋:
一. YouTube片段「We Too」
二. For sale: a sliver of sidewalk and other ‘challenging’ L.A. properties
三.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where are they and who owns them?
四. Mass trespass of Kinder Sc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