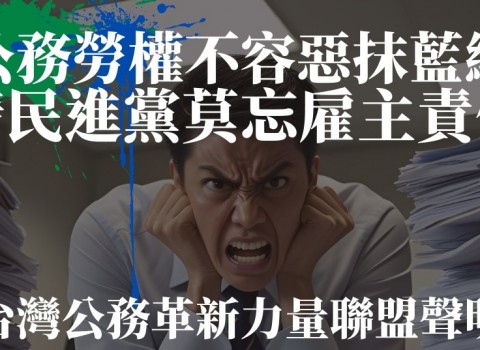(左起:林凱衡、鄭中睿、何撒娜、許仁碩/照片來源:台灣勞動者協會)
編寫/林奕志(台灣勞動者協會理事)
本文為去(2021)年五一勞動影展,「可拋棄式勞工」放映專題座談(「勞動彈性化與工作貧窮下的東亞工人運動」)紀要。今(2022)年影展,將於4月22至30日,在台中、高雄、台南、嘉義、桃園、新北巡迴放映;完整片單、場次及影片詳細介紹,可至影展官網查詢。
1970年代後期,在西方經濟危機背景下,歐美許多企業為因應市場波動、「彈性」管控成本,開始縮減組織規模、業務,將原本直接聘僱、經評估為「非核心」的人力,大量以委外、臨時人力、部分工時替代。而到了1990年代,這樣源自歐美的「彈性」浪潮進入東亞,區域內各國(尤其日、韓)非典型僱用迅速氾濫。
過去四十多年,與「勞動彈性化」的全球發展、擴張同步,世界各國的工會組織率普遍、顯著下降;裂解了基於工人階級團結與國家管制的社會保護,破壞就業安全、惡化勞動條件,造成日愈廣泛、嚴重的「工作貧窮」現象。而在日本、南韓及台灣,由於工會運動傳統上以企業工會為主力,既有具資源、實力的大工會們(通常由國營或大型私人企業裡的正式勞工組成),一般不太容易有動機去組織所屬企業以外的勞工(即便是自家公司使用的派遣、承攬勞工);故,面對勞動彈性化之拆解僱用身份一致與連帶工人團結基礎,工運受到的打擊比歐美更為嚴重,遭遇的挑戰更加艱鉅。
針對上述狀況,去年五一勞動影展,請來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許仁碩(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助理教授)、鄭中睿(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顧問),以「勞動彈性化與工作貧窮下的東亞工人運動」為題進行座談,由林凱衡(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擔任主持人。下文,為該場座談紀要。

何撒娜(照片來源:台灣勞動者協會)
韓國
金融風暴成為派遣元凶
座談由何撒娜首先發言。何撒娜指出,韓國雇用關係從傳統且富有人情味的終身雇用制轉變,主要來自於1997年與2008年的金融風暴。1997年韓國金融風暴後,被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勢介入,允許外資進入以及惡意併購,也造成韓國的終身雇用制面臨瓦解,臨時工與派遣制度的擴張。
而2008年的金融風暴,又將這個狀況再度惡化。其中包含韓國大財閥的擴張,韓國的大財閥一直是國家經濟的主體,在2008年之前,GDP中前10大財閥的占比已經達到50%,在2008年至2010年的2年間,更增加到75%。中小企業大量破產,勞工成為大企業的派遣工,使得派遣勞動等非典型雇用的狀況更加的嚴峻。
以2019年為例,南韓2,550萬名的勞工中,已經有748萬的非典型雇用勞工,接近30%的比例。而正式僱用的勞工月薪平均是323萬韓元,約7萬6千台幣,非典雇用的勞工約只有正式勞工的一半的171萬韓元,相當於4萬元台幣。且非典雇用的狀況在青年勞動人口(15歲~29歲)中更加嚴重,比例從2003年的31.8%增加到2019的40.10%。年輕勞動者的非典雇用幾乎成為了常態。
何撒娜說明,從畢業生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年齡為例,可看出這種常態狀況。過去韓國年輕人大約在25歲可以找到第1份正式工作,但現在居然推遲到了31歲。雖然疫情也有影響,可以想像非典型雇用的趨勢對南韓年輕族群的影響巨大。除了年輕人,南韓的非典雇用中,女性也占了比較高的比例,達到了55.1%。且因為職場升遷被家庭照顧中斷的關係,女性就算重回職場,她們的薪水只有平均月薪323萬韓元的1/4的80萬韓元左右。
南韓的派遣勞工與工會
南韓的派遣勞工,雖然沒有像南韓的傳統工會形成強大的工會組織,但他們的集體行動力還是很強的,何撒娜認為這與南韓的社會狀況有關係。南韓社會對於「共同體」的想像非常強大,這造就了強大的工會傳統,因為他們不會認為這只是自己的事,而是整個社會都有責任。所以傳統工會與派遣勞工雖然沒有直接上的組織關係,但是互相的支援是比較多的,派遣或非典勞工的集體行動也還是比較多與比較有力量。

許仁碩(照片來源:台灣勞動者協會)
日本
終身僱用制與非典勞動的推力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終身僱用制。許仁碩指出終身僱用制的特色之一,是大部分的大學生都會在畢業之前展開漫長的求職活動,通常持續1年左右,也就是整個大四。然後在畢業前拿到某間公司的聘約,畢業後直接進入公司工作。
與台灣大部分的工作狀況不同的是,他們應徵的並不是特定的工作職位,例如法務、業務、會計,而是「公司員工」,工作內容與地點都是到職後任由公司決定與調動,例如不是唸法律的也可能被分發到法務部門。所以新人薪水一致且偏低,但會隨年資增加,順利的話,能在一間公司從年輕做到退休。這是日本勞工的理想設定。且如果進入婚姻,也會給予相應的育兒、家庭津貼。這些津貼相當優渥,預設配偶不須再去工作,或頂多打工即可。
上述狀況提供了一個非典勞動的推力。因為大部分的終身僱用制度所僱用的是男性,而女性通常會因為婚育辭職,再回到職場後已經很難有好的工作。而且因領取配偶津貼的條件是配偶(多半是妻子)的薪資所得,須低於一般全職員工水平。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否實際領有配偶津貼,對重回職場的已婚婦女給予低薪的做法,長年被視為理所當然,這也提供了勞動派遣等非典型雇用良好的發展環境。
另外,若在大學畢業前沒有找到工作,也很難有翻身的機會。許仁碩說,日本的公司不像台灣,隨時都可以應徵,沒有在大四畢業前找到工作,就幾乎沒有機會成為終身雇用制的一員。這些被排除在終身雇用之外的勞工,即成為所謂的飛特族(freeter)或打工族,長期處於就業不穩定,薪水較低的非典勞動處境。
傳統工會與非典勞工。
日本勞工運動在1970年代有罷工的高峰期,與資方的對抗意識強烈,而到了1980年代,工會與資方的關係開始轉變。日本工會的組織率一度相當高,許多企業都有70%~90%,工會力量強大,公司為了避免罷工,會盡可能回應工會的訴求。勞工運動也形成春鬥的傳統。即便現在幾乎不再罷工,每年春季時,大工會仍會集體提出提高勞動條件的要求,政府也會給資方壓力,資方也通常會給予一定的回應,成為相當制度化的「春鬥」。
但在這樣的過程中,沒有被正式雇用的非典勞工,包含派遣、飛特族與打工族就被拋棄了。因為沒有被納入正規的勞動體系,傳統企業工會也不認為他們是「自己人」,透過春鬥等改善的勞動條件,也鮮少惠及非典勞工。而這些非典勞工,則開始嘗試自行組織,但因為非典勞工的流動率高、散落四處,且各自的認知有差異,無法形成一個對資方有談判力的勞工組織,更像是社會議題的倡議團體。
但許仁碩指出因為這些以非典勞動為主要關注對象的組織與團體,揭露了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的「非主流勞工」階級的現實狀況,才讓日本社會對於這些非典勞動者的處境被看到。這些團體大約在2000年前後開始活躍且被關注,且在2009年的時候促成了日本的政黨輪替。

鄭中睿(照片來源:台灣勞動者協會)
台灣
台灣因相對日、韓,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勞動力市場本來就比較零散,「彈性化」轉變並不顯得那麼戲劇性、劇烈。不過,鄭中睿也指出,台灣派遣勞工的人數,有被低估的可能。在日本跟韓國,人力派遣是特許行業,政府相關統計的準確度比台灣高很多。
台灣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官方對非典型勞動的調查,種類及樣本數都非常不足,可以合理懷疑沒有呈現實際狀況。但,從有限的數據裡,還是可以看到2008年(政府首次調查非典型勞工人數)到2020年,台灣非典型勞動者的官方統計人數,成長率約20%;相對,全體勞工僅為10%左右,非典型勞動的擴張趨勢仍稱得上顯著。
最後,鄭中睿表示,台灣工運雖然也意識到勞動彈性化對勞工的傷害,但受制於各種原因,比較有規模、實力的工會們,並未積極組織非典型勞工。近年,少數值得一提,非典型勞動者組織起來的正面案例,有2014年公共電視派遣工、2019年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民台)勞務承攬人員納編轉正,以及2016年,「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成立,主要針對公部門中藍領性質的派遣、承攬勞工(清潔、保全、傳送、駕駛等),進行組織工作。儘管這幾個工會的力量都還不強,但鄭中睿說,自己仍從中看到希望。
(逐字稿:陳知妤、林若芷、李品蓁、陳郁勛)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