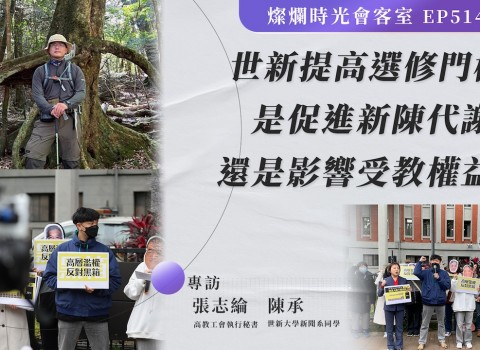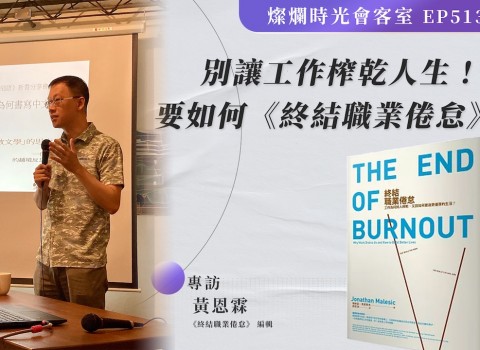文 / 李芸屏
2023年1月7號,立法院三讀通過《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正案,前立法委員,同時也是小燈泡的媽媽王婉諭,深感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不足,進入立法院後就致力於推動法案的修正。
為何會感到權益得不到足夠保障?修法又能如何幫助被害人,並讓整體社會變得更好?本集節目邀請王婉諭來談她的自身經驗,以及她推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的動機與目的。
消失的被害人聲音 在司法制度下的多重身心壓力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中的犯罪被害人,指的是死亡、重傷或受到性侵害的被害人,曾經歷小燈泡事件的犯罪被害人家屬王婉諭說,多數被害人及其家屬其實背負重重壓力,事發當下必須煩惱是否要解剖遺體,以及何時可以領回遺體等問題,事發後更因不熟悉訴訟流程,對法院感到擔憂和恐懼,此外,被害人也可能面對大量媒體的壓力,她表示當時就有媒體直接住在她家社區門口守她。
但創傷並不僅是短期的傷痛,王婉諭指出,被害人首先必須面對數年的司法訴訟,以及長期心理創傷的復原,例如性侵案件的被害人面對外界的目光與譴責,不一定敢於坦露自身經歷,重傷和遭性侵的被害人則必須花費龐大費用幫助身體復健,以及處理因身體創傷而必須重新安頓、調整生活模式等問題。
司法制度還會導致對被害人二次傷害,王婉諭說,即便當時「小燈泡事件」受矚目讓她得到許多援助,但她仍感不適。例如,「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告知她可以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但申請後才得知補償金必須通過法院審議,開庭時審議委員坐在法庭高處對她說:「你現在還吃得下飯嗎?」「有必要用到這麼高的費用嗎?」,王婉諭不解為何心痛的被害者還要面對不合情理的對待?儘管她理解審議目的在於釐清事件以便確認給付金額,但過程卻造成被害人二次傷害,她認為,犯保機構受檢察體系管轄,審議委員皆來自檢察體系,導致過程缺乏其他專業的意見而無法貼近被害人的處境。
此外,雖然王婉諭當時可以與檢察官討論並發表意見,但實際上司法訴訟的體系中僅有「審檢辯」三方角色,被害人無法參與其中,亦不能與檢察官互動、討論,當被害人家屬的意見與檢察官不同時就可能導致意見不被採納。
而原本的開庭制度也存在問題,王婉諭說,在進入法庭前就會先確認當事人的身分證是否為當事人,但開庭時法官又會再次宣讀確認當事人的地址、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對當時被媒體守在家門不堪其擾的王婉諭來說,更恐懼個人資料會被他人知道,這讓她察覺整體的司法流程缺乏對被害人的理解,因此也在擔任立委時做出調整。
國家角色缺失 被漏接的被害人
王婉諭說,在訪談多名被害人後,才知道即便法規已經明確定義哪類被害人可以得到國家協助,但實際上仍有半數以上的被害人未獲協助。由於通報系統的責任歸屬沒有被明確界定,導致警察、檢察體系、司法體系雖可以通知犯保協會協助被害人,但最後也可能沒有單位通知。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和犯保協會量能有關,由於每個分會僅有兩到三名正職人員服務,以致漏接許多案件,大多數被害者孤立無援。政府往往認為被害人的救濟並非國家的責任,但王婉諭認為犯罪事件的發生不僅是行為人本身的問題,而是制度有問題。例如精神障礙者在犯下案件之前,國家是否讓他能事前就獲得支持,或道路標號的設計、執法的嚴謹程度,都可能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她認為國家在犯罪事件中必須負擔一定責任,被害人得到的協助並非國家給予的恩惠,而應該是基本權益的保障。
修法,讓協助成為基本的權益保障
此次修法調正幅度極大,以補償金的審議為例,王婉諭指出,過去補償是以代位求償為原則,若國家無法從被告處取得補償金,最後會收回原先給被害者的補償,但王婉諭認為補償是被害人的權益,國家需負責給予保障,因此除了改為給付行政,以國家角色給予補償外,同時也將補償制度改以定額給付,如死亡或受重傷等皆明訂不同分級的給付金額,採簡易審查避免原本因詢問不同細項導致被害人受到二次傷害的問題。
此外,原先的審議制度中僅有檢察體系的成員,難以同理、親近被害人的處境,王婉諭認為審議委員應該由不同專業組成,因此本次修法也明定犯保協會的成員應包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社工師等對被害人權益保障有研究的專家。
至於原先制度中未明確定義負責通報犯保協會的單位,則改為當相關單位執行勤務的時候發現被害人或家屬符合資格時應主動詢問 、告知案件進程並提供協助,若被害人不符合法律扶助的經濟條件限制,犯保協會也應給予法律協助。王婉諭說,檢察官曾經告知她可以上網查詢案件何時會被起訴,但對被害人而言,在處理身心創傷的同時又要持續追蹤案件進程相當困難,而不希望被打擾的被害人,也應該受到尊重。
經費足夠 卻被忽略的基礎建設
依據2021年犯保協會的統計,法律服務次數是25422人,諮商服務人次54000人,這也顯示出犯保協會大量的人力需求,但受限於人力和經費不足,過往平均一名專任人員必須協助近兩百名被害人,有時甚至會被挪用於宣傳反詐騙、賄選活動,因此若要增加犯保協會成員、強化成員和志工的培訓與遴選制度,勢必得增加經費。王婉諭表示,他們原先希望仿照法扶成立基金,由國家定期給予預算,但政府以財團法人捐助經費的名額已滿為由拒絕,她說,儘管許多人都會疑惑國家經費是否足夠,但在進入立法院後她才發現許多經費都被投注在一次性的政策上而非基礎建設,王婉諭說,國家經費其實足夠,問題在於缺乏有效分配,且忽略基礎建設的重要性,才會將經費投入在一次性政策上。
修復式司法 盼類似案件不再發生
此次修法也增訂修復式司法相關條文,盼能修復犯罪者與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傷害。王婉諭說,她原本並不清楚何謂修復式司法,但她認為沒有人一出生就想犯罪,在犯罪前的成長過程才是造成結果的原因,然而傳統的司法過程並不能解決她的困惑,這也讓她走上修復式司法的道路。儘管並不是直接對話,但透過爬梳王景玉的生命史,讓她看見對方在成長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這也是雖然修復式司法沒有順利完成,但她仍然決定先放下的原因。
不過,王婉諭指出,修復式司法目前在台灣的制度並不完善,也不普及,如何讓被害人有充足知情權、了解修復式司法的內涵和意義,進而決定是否參與,都是推行修復式司法的重點與難點之一。此外,目前修復式司法中的修復促進者以志工為主,缺乏嚴謹的訓練機制導致專業度不足。王婉諭以她遇到的促進者為例,不僅在案件處理過程中洩漏犯罪者的個人資訊,甚至洩漏促進者以前處理的案件中其他當事人的資訊。她也曾遇到一位促進者告訴她:「你的孩子離開其實已經有讓大家改變很多了,比如說在母親節的時候發了很多『孝字』的饅頭。」儘管她能理解促進者出於好意,卻難以從這樣的話語中得到安慰。她也表示,修法並不代表法律會被落實,官僚文化、法案的優先順序和勞動條件等因素都可能影響法律是否會被持續執行。管中祥也補充,在有仇必報的傳統司法思維下,被害者不一定會願意參與修復式司法並與加害者和解,這樣的文化也是推行修復式司法的阻礙之一。
不過,王婉諭認為修復式司法仍然可能達成,在她的參與經驗中,修復式司法的調查完整度與深度遠遠超出傳統司法,顯示國家其實能做到修復式司法,重點在於國家是否在乎這種長遠的基礎工程。她表示,許多政策其實是在辦公室中制定的,官方並不了解實際狀況,政策無法對症下藥,而就司法案件來說,根本的問題在於加害者為何犯案、犯案前期是否能夠阻止,以及犯案後是否可能再犯,修復式司法就是希望了解犯案原因並制定政策,未來才能避免更多案件發生。她也以自身經驗為例,指出目前台灣的心理健康問題與自殺率逐年攀升,當精神障礙者在前期的心理健康不受關注,甚至更前期兒少的心理健康和自殺率不受重視,學校輔導資源不足,一連串問題累積,最終才導致特定結果發生,當社會成本沒有投注在前期預防,勢必就得在後期承擔相應的後果,這也是為何她認為保障被害人權益、推行修復式司法並了解犯罪者的成因,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其實有利於整體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