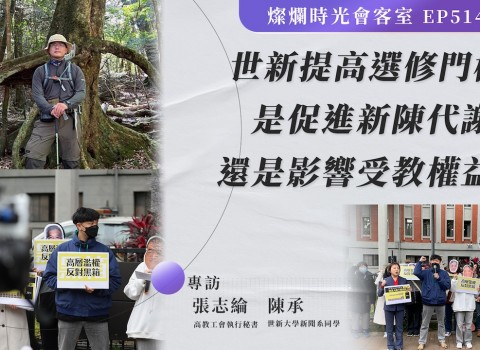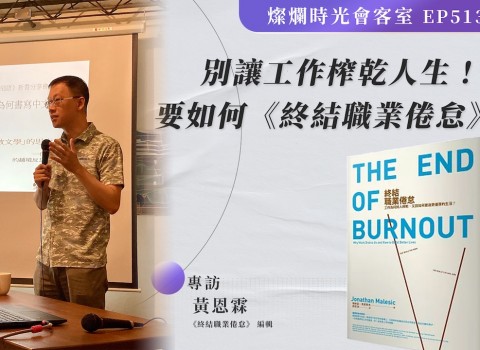文 / 曾霈榆
即將在公視播出的台灣首部二戰懸疑劇集《聽海湧》,描繪日治時代被日本徵召的台灣青年,飄洋過海至婆羅洲替日軍監看戰俘,過程中被捲入一場冷血屠殺,在戰後更遭國際法庭澳洲檢察官指控犯下虐待戰俘罪行,面臨世紀審判。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聽海湧》導演孫介珩,一同了解該劇為何以「台籍戰俘監視員」作為故事主角?為了符合劇中年代設定,演員們做了哪些準備?導演與編劇如何針對這段歷史進行田野調查與文獻蒐集?面對劇中角色複雜的身分認同,現今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又該如何思考與理解?
歷史人的好奇心 看見戰火下「人」的多元樣貌
「我們歷史系有一個人格特質,對故事會有興趣,甚至會有一些敏感度。」從歷史系畢業的導演孫介珩表示,他曾對歷史課本上一張台灣光復受降典禮的照片感到好奇,照片裡的日本軍官神情哀戚,中華民國代表則開心地接下受降書,周遭被眾多台灣觀禮群眾所包圍,但照片中這些台灣人的表情卻是模糊的,他開始思考當時台灣人對政權轉移的態度究竟是好是壞?面對身分、語言、教育以及認同的劇烈轉變,那時的台灣人該如何面對?
《聽海湧》的三位主角是在二戰時期擔任台籍戰俘監視員。孫介珩表示,在研究題材時,發現台籍戰俘監視員的職位十分具有戲劇張力,負責替日軍看管戰俘,在戰爭結束的那刻,卻沒有獲得自由,因為戰俘監視員並非士兵,在戰爭期間以暴力、不人道手段管理戰俘被視為違法行為,導致被送上了國際法庭。但在國際法庭上,主要由說英文的澳洲人主持,因語言隔閡,即使有翻譯員,也只能以非台灣人母語的日語回答,再由翻譯員翻譯成英文溝通,台灣人往往難以為自身答辯。孫介珩認為,戰爭結束後,當事人可能面臨五年、十年的刑期,但這些經驗卻永久烙印在他們身上,難以忘卻,他想呈現人類在戰爭下並非只有單一面孔,透由劇中主角三兄弟截然不同的參軍理由及個性,凸顯出當時台籍日本兵的多元樣貌。
主持人管中祥表示,一部好看的劇主角往往處於尷尬的角色,在面臨選擇時總是左右為難,在看《聽海湧》時,讓他聯想到了描述同樣時代背景的紀錄片《由島至島》,講述二戰替日本人翻譯的台籍翻譯員故事,與台籍戰俘監視員的角色定位類似,雖然不是主要犯罪者,卻也離不開幫兇的罪名。
田調蒐集多方資料 以此為基礎創作
孫介珩分享,在戲劇前期田野調查過程中,透過澳洲軍方、日本律師以及台籍日本兵等不同立場的資料蒐集,得以了解當年台籍戰俘監視員的審判如何進行,並以此基礎進行創作,拍出屬於台灣人的故事。
孫介珩表示,歐美國家或日本在二戰結束後,便緊鑼密鼓地開始進行回憶錄的訪談,蒐集戰爭資料,而台灣卻隨即面臨戒嚴,具戰爭經驗的老兵難以訴說他們的經歷,直至解嚴後學者才開始進行口述歷史調查。他進一步表示,口述歷史往往是主觀的個人經驗,長年不曾分享這段戰爭經歷的老兵,在描述時可能會遺忘或隱藏某部分內容,讓他難以掌握內容的準確性。因此,在閱讀完口述歷史資料後,他試圖整理當時客觀發生的事件,至澳洲戰爭紀念館的線上資料庫,翻閱當時的國際軍事資料,查找檔案所記載的台籍日本兵姓名,瞭解當年發生的暴力毆打及屠殺始末。另外,他也研究當時至南洋協助日本兵辯護的日本律師留下的紀錄,當中提及許多台籍日本兵的描述,讓他得以更接近二戰後台籍戰俘監視員審判的真相。
不過孫介珩坦言,即使多方資料拼湊比對,這段歷史仍不一定客觀,例如當時澳洲的法庭審判因語言隔閡,對母語非英語及日語的台灣人而言,難以精準傳達當時情況,對判決恐有很大影響。
拒絕單一標籤 呈現每個人在戰爭下的選擇
經過長時間的歷史資料爬梳後,孫介珩表示,起初常感嘆台灣人是個動盪的民族,遭日本人派遣至南洋,被迫做了許多不堪之事,常從台灣人的角度想像戰爭當下發生的種種。然而,隨著後續資料蒐集愈來愈多,卻發現有些台灣人在當地人眼中確實是「幫兇」的角色,特別是對東南亞華人而言,他們認為明明說著相同語言的台灣人,竟然不幫自己,反而協助日本人來迫害他們,對台籍戰俘監視員充斥著不諒解及恨意。但他也蒐集到一些案例,提及部分台籍戰俘監視員對當地人十分友善,特別感謝他們。
「我們很難用臉譜化或標籤來解釋這件事情,每個人的個性與選擇,在戰爭這種很極端的情況下,都會是不一樣的。」孫介珩說,在劇中想要呈現儘管同是台灣人,身處同一處境,每個人仍會做出不同決定,而這也會影響到他們未來如何和這場戰爭共處。
「人會選擇殘暴、殘忍,做出不理性的決定,一定是環境使然。」孫介珩認為,劇中的角色設計皆回到「人性」思考,脫掉角色的國籍外衣,沒有誰是誰非,以劇中三位主角為例,在當時,身分認同混亂的台灣人搞不清對方是敵是友,在戰爭時與日本人並肩作戰,但戰後卻成為了敵人,在這樣的矛盾與尷尬下,只能不斷地思考與辯證,也更能貼近當時台灣人面臨的困境。
孫介珩表示,他想透過《聽海湧》找到台灣社會理想的社會狀態,在看第一集時,可以對這些出場的角色抱持著好惡的立場,但到最後一集時,可以回頭問自己當初認同的角色,真的是好人嗎?當初討厭的那個角色,真的這麼邪惡嗎?他希望觀眾能從這部片子中看見自己的家族記憶,或許有些人的父執輩曾至南洋當過日本兵,或者在日本時代生活過,而某部分觀眾的家族可能是1949年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台,他們將會看到在同一時間點下很不一樣的台灣故事,也期望未來在討論認同議題時,台灣人能有更多理解與包容,
人物設定考究 五集訴說大時代故事
《聽海湧》雖然僅短短五集,卻耗費長達四年拍攝,加上戰爭題材在台灣較冷門,導演和主創團隊一邊籌備一邊找錢,製作成本高,平均一集的預算超過一千萬。至於為何只有五集,孫介珩表示,他和編劇很喜歡《核爆家園》這齣劇,以車諾比核災的真實事件作為背景,運用人物在事件中穿針引線,除了帶出事件經過,也能從中洞察人性的糾葛與複雜性,而《聽海湧》中的台籍戰俘監視員也是相同的做法,這群台籍戰俘監視員具有一定人數,更影響了許多家族,其任職時間點有明確的開始與結束,因此他認為以五集的長度來訴說這個故事十分合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時代下,劇中出現來自不同國家的角色,對演員是一大挑戰,除了語言需流利外,說話方式與語調也要符合時代背景。孫介珩表示,主角三兄弟使用的主要語言為日語及台語,由於他們在日本時代出生,當時的國語為日語,對日語的要求需要非常流利,因此演員早在半年前便開始集訓上日語課,更讓他們體驗真實身在日本社會中,讓演員從語言、文化及思想上能想像當時在日本社會生存的模樣。而澳洲檢察官的角色為了還原80年前的澳洲腔,演員十分認真做功課,找到1940、1950年代的澳洲廣播音檔,發現當時上層階級的澳洲人說話更偏向英腔,平民階層腔調則較平,勞工階層則如同今日印象中的澳洲腔,經過討論後,想像這位澳洲軍官的家族世代從軍,因此設定角色偏向英腔口音。
一度將面臨停拍 三餘創投成資金及時雨
在《聽海湧》的製作名單中,能發現三餘創投出現在聯合出品名單中,他們的加入對拍攝團隊而言是資金的及時雨。孫介珩透露,劇組拍攝期的六十天是最燒錢的時候,資金調度龐大,作為最大出資者的公共電視的資金採分期給付,收入一度趕不上支出速度,將面臨停拍。這時三餘書店初成立三餘創投,期望開展書店外的文化投資,經過三餘書店內部討論後決定投資,讓劇組得以繼續完成拍攝。
除了常見的社群宣傳外,《聽海湧》也特別安排獨立書店的座談宣傳。孫介珩表示,他從小很喜歡逛書店,對他而言書店是很重要的精神支柱,且他想要透過一、兩個小時的座談,和觀眾慢慢聊劇中的許多角色設計、議題與歷史田調考究,期望與有興趣的觀眾互動,了解他們對這齣劇的好奇與感受,因此選擇獨立書店座談作為宣傳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