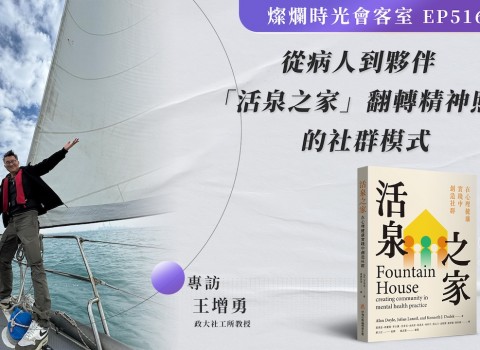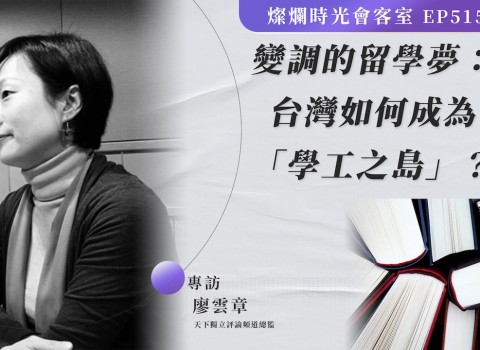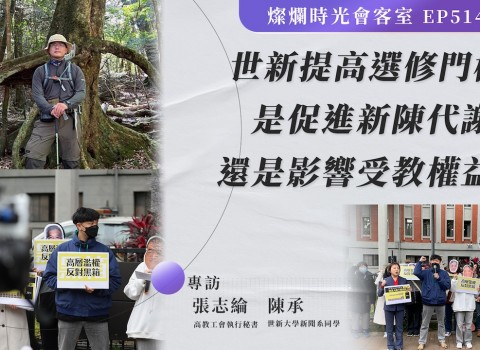文 / 黃苡甄
台大社工系畢業的楊小豌是位助人工作者,經常穿梭於社會與少數族群之間。每當她與少數族群接觸,總能深刻感受他們的情緒與困境,與個案產生共鳴的同時,也在這段旅程中不斷成長。
在《街頭流離者》書中,她分享了與無家者互動的點滴,希望藉由具體行動與真實故事,種下一顆改變的種子,促進社會對話,讓理解逐漸萌芽、堆疊,讓社會更深入認識助人工作者的角色與少數群體的處境。
打破老窮無家者印象 無家者露宿街頭的實際原因
大眾對無家者的印象多停留在年長且貧困的族群。實際上,許多年輕人也面臨無家可歸的處境。許多人或許會疑惑,為何這些年輕人不去工作,而是流浪街頭?他們自身又如何看待這種生活?
楊小豌分享,無家者的組成與背景各有差異,年輕人的流離歷往往與家庭背景、社會環境息息相關。有些人可能在不穩定的家庭環境中成長,早早便須獨立謀生。他們的生活充滿波折,當遭遇經濟困難或無法找到棲身之處時,可能只能選擇露宿街頭。這些人的處境並非單純因為「不努力」,而是與社會結構、資源分配密切相關。另一些長期露宿的年輕無家者,可能是性別少數群體或具有身心障礙,家庭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持,從小習慣依賴社會補助,缺乏足夠的教育資源與就業規劃,使他們更難脫離流浪的生活。此外,某些年輕人甚至因為家庭的管控與壓抑,選擇露宿作為逃離原生家庭的方式,反而希望藉此爭取自主生活的可能性。
楊小豌提到,接觸年輕無家者的過程中,引發許多自我反思。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擁有某種社會特權,例如良好的教育環境、較佳的表達能力。這些資源並非全然來自個人的努力,而是受到家庭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與其單純將無家者的困境歸咎於個人選擇,不如進一步思考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個體的發展機會。
更值得關注的是,無家者的議題並不僅限於年輕男性,還包括女性無家者群體,她們的經歷往往更加隱形,卻同樣值得探討。
女性無家者的生存法則
女性無家者的街頭生活,往往面臨更高的風險,因此發展出不同的生存策略來保護自己。楊小豌說,部分女性無家者透過改變外貌,例如:剃平頭、穿著較中性的衣物,甚至使用多條皮帶來增加衣物的安全性,使自己看起來較為陽剛、難以親近,減少露宿在街頭時潛在的騷擾或攻擊,這種刻意營造出的距離感,讓她們不會輕易被「找麻煩」。另一部分女性則選擇依附於特定的男性,換取物資或提升自身的安全感。有些女性會在伴侶入獄後,迅速與其他男性建立關係,確保自己在街頭的基本生存條件。雖然這種方式可能受到外界的「誤解」,但在艱難的生活環境中,這成為了一種常見的生存策略。
此外,長期處於不安與高度警戒的狀態,也會對女性無家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影響。由於夜間街頭的不安全性,許多女性選擇待在便利商店內,導致長期失眠、身體疲勞,甚至出現焦慮與神經質的傾向。有些女性在街頭生活久了,變得更加敏感,甚至會對他人無意間的碰觸產生強烈的防備心理,進一步影響她們的社交能力與心理狀態。
在這樣的困境下,部分社會組織如慈善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會,提供服務給需要庇護的女性,幫助她們找到更穩定的生活空間。此外,除了實際露宿街頭的女性無家者外,還有許多「類遊民」的存在,楊小豌說,疫情之後,「類遊民」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例如即將面臨驅逐的高齡者、暫時借宿朋友家但無法長久安身的女性等。
女性無家者的困境往往比男性更為隱形,因為在真正流落街頭前,她們往往會選擇其他替代方案,如投靠男性友人、住進原生家庭的親屬家中。然而,這樣的選擇並不一定能帶來真正的安全,部分女性甚至在這些環境中遭受性暴力或肢體侵害,陷入「有屋簷但面對暴力」與「露宿街頭但風險未知」的兩難處境。
為何無家者通常有不穩定的身心狀況 社會如何協助他們?
無家者群體中有相當比例的人面臨精神健康問題,這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部分無家者可能因精神疾病導致生活更加困難,甚至可能讓社會大眾產生誤解或恐懼,擔心他們具有攻擊性。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簡單。
一些無家者的精神健康問題可能與過去的生活經歷相關。楊小豌說,部分年輕的無家者曾因毒品問題進出監獄,在離開原有的社會支持系統後,回到街頭時又容易與過去的毒品相關人脈「重逢」。長期使用毒品可能對大腦造成永久性損傷,使得這些人難以維持穩定的治療與用藥習慣。此外,經濟困境也使得部分無家者優先選擇購買菸酒緩解短期不適,而非醫療照護上。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台北市社會局與「街頭家醫計畫」提供的就診補助單,幫助無家者獲得精神科診療。然而,診療過程中也存在許多挑戰,例如長時間候診可能加劇無家者的焦慮,或是藥物管理困難等問題,部分無家者甚至可能轉賣藥物以換取現金。楊小豌說:「陪伴真的就是能不能穩定他的身心狀況的第一步,就是我要怎麼讓他跟我有信任關係。」這些問題使得助人工作者在提供協助時,必須與無家者建立信任關係,並持續關注他們的狀況,確保醫療資源能夠真正發揮作用。
除了無家者,一些曾服刑多年、刑滿出獄的人也面臨社會適應困難。這些人可能因過去的犯罪紀錄在求職時遇到困難,而再次陷入「非法活動」的循環。社會貼在前科者身上的標籤,使得他們即使有悔改與回饋社會的意願,仍難以獲得信任與機會,顯示出社會安全網的不足與結構性的挑戰。
楊小豌說明,「社會復歸」的過程中,他們往往面臨多重困境,包括經濟壓力、精神健康問題、社會歧視等。不過還是有人希望改變自身處境,努力向上發展。她說:「其實人是會改變的。其實人是會有渴望,也是能夠學習,渴望有對於自己感到愧疚的人能夠有所補償,然後對社會他能夠有所回饋。」
命運的枷鎖 尋覓希望之光
經濟的限制不僅影響個人,也決定了他們的社交圈與資訊來源。例如,當一個人的朋友圈普遍面臨經濟壓力時,彼此之間的討論焦點多半圍繞在生存問題上而非長遠規劃。因此,當社會對這些群體產生質疑,認為他們為何不做出更好的選擇時,往往忽略了環境對人的影響。一個人的成長背景、家庭文化與朋友圈,決定了他所接觸到的價值觀與行動模式。如果成長過程中缺乏正向的引導,那麼他們為了生存所作的選擇,便顯得不可避免。
楊小豌以書中提到的阿源為例,他過去的黑道背景,因為家庭與社會對待母親的態度,使他走上了以暴力解決問題的道路,最終犯下殺人罪,並在多年後成為無家者。現今的他時常藉由酒精麻痺自己,身邊的朋友也習慣將他視為類似大哥的存在。即使他的外在表現彷彿一蹋糊塗,但仍然可以看到他作為人的尊嚴與內心的美好。
楊小豌說,其實,人與生俱來都有其美好與尊嚴,我仍然相信這份價值是真實存在的。只是,它需要一些時間,去撥開來看見。
社會服務的種子如何在行動中發芽
社會服務與倡議的投入是否真的能帶來改變?楊小豌分享,自己所從事的不僅僅是第一線的直接服務,也包括倡議與社會對話的工作。透過這些行動,不僅能影響受助者,還能讓更多人參與其中。原本只專注於個人生活與工作的志工,可能會願意每週花一個晚上的時間,與無家者交流、陪伴他們,進而改變自身的視角與態度。這樣的影響如同種子一般,逐漸在社會中萌芽。
她回憶起自己尚未成為社工時,曾邀請一位有藝術背景的朋友參與街頭關懷行動。起初,這位朋友對陌生的街頭環境感到不安,但因為有團隊的陪伴,她克服了恐懼,勇敢地踏入這個場域。後來,她在麥當勞看到一位疑似無家者的大姐,便鼓起勇氣主動攀談,甚至畫了一幅畫送給對方,讓那位大姐度過了一天美好的時光。這樣的小小行動,讓人看見善意與連結的可能性,也證明了社會關懷並非遙不可及,而是可以透過一次次的互動來實現。
許多身處困境的人並非一開始就與社會脫節,而是在經歷關係破裂、人生意外後,逐漸被孤立,若能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哪怕只是一次簡單的陪伴與對話,都可能成為改變的契機。楊小豌認為,透過這樣的關懷行動,不僅能讓受助者感受到溫暖,也能促使參與者思考自身與社會的關係,甚至學會更謙卑地面對生活。
改變往往是緩慢且難以察覺的,但如果不開始行動,就永遠不會有任何改變,即便過程緩慢,只要持續努力,累積的影響力終將展現。社會工作、社會服務、甚至社會運動,都不是單一事件的刺激反應,而是透過不斷參與、體會與行動,逐漸內化為個人與集體的價值觀,最終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慢下來 聆聽他人故事 感受自己情緒
楊小豌說,在擔任社工或關心無家者的工作過程中,會遇到各種挑戰與挫折。這些挑戰不僅來自於制度與社會現實,也包含她與服務對象的互動,甚至是本身情緒的起伏。她坦言,自己天性情緒起伏不大,往往在一天結束後才會回顧並整理當天的疲憊與影響,然而,助人工作的其中一個挑戰在於,社工不僅是觀察者,更需要成為維持秩序、設立界線的人。例如,在據點管理中,有些無家者因飲酒過量或違反規定而被請離,但這樣的過程往往並不順利,甚至會遭到反抗與辱罵。這樣的場景讓她不得不在某些時刻「武裝」自己,展現出一種嚴厲的態度,以避免被看輕或挑戰權威。
這並不是她的本性,因此每一次的強硬態度都讓她感到耗費心力。她意識到,在助人工作中,學習如何設立界線、表達自身立場,是一種必要的練習。她將這段經歷視為個人成長的一部分,就像人類學研究中的自我觀察。楊小豌認為,助人工作的價值不僅在於陪伴他人,也包含學習如何更好地陪伴自己,讓自己保持穩定,才有餘力幫助他人。
她也說,「流離」這個概念並不總是負面的。有些無家者的離開並非單純被社會淘汰,而是一種自主選擇,或許是逃離暴力的家庭,或許是尋找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在流動的過程中,重新適應環境,並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生存之道。「這個社會到底是誰在淘汰人?又憑什麼淘汰人?」如果社會的運作方式使許多人在未經選擇的情況下被迫退出,這不僅是一種個人危機,更是一種集體危機。談到「不淘汰人的社會」,楊小豌說:「對我來說是我們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淘汰。」
真正的社會安全網並不是將某些人隔離以確保整體的安全,而是要讓社會能夠接住每一個人。這個社會應該有足夠的包容性與支持系統,讓所有人都能有生存與發展的機會。雖然她不認為自己在有生之年能見證一個「完全不淘汰人的社會」。但是楊小豌相信,只要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並願意為之努力,我們仍然可以共同編織一張更安全、更具包容性的社會安全網。即使這條路漫長且充滿挑戰,願意開始思考並行動,便已是改變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