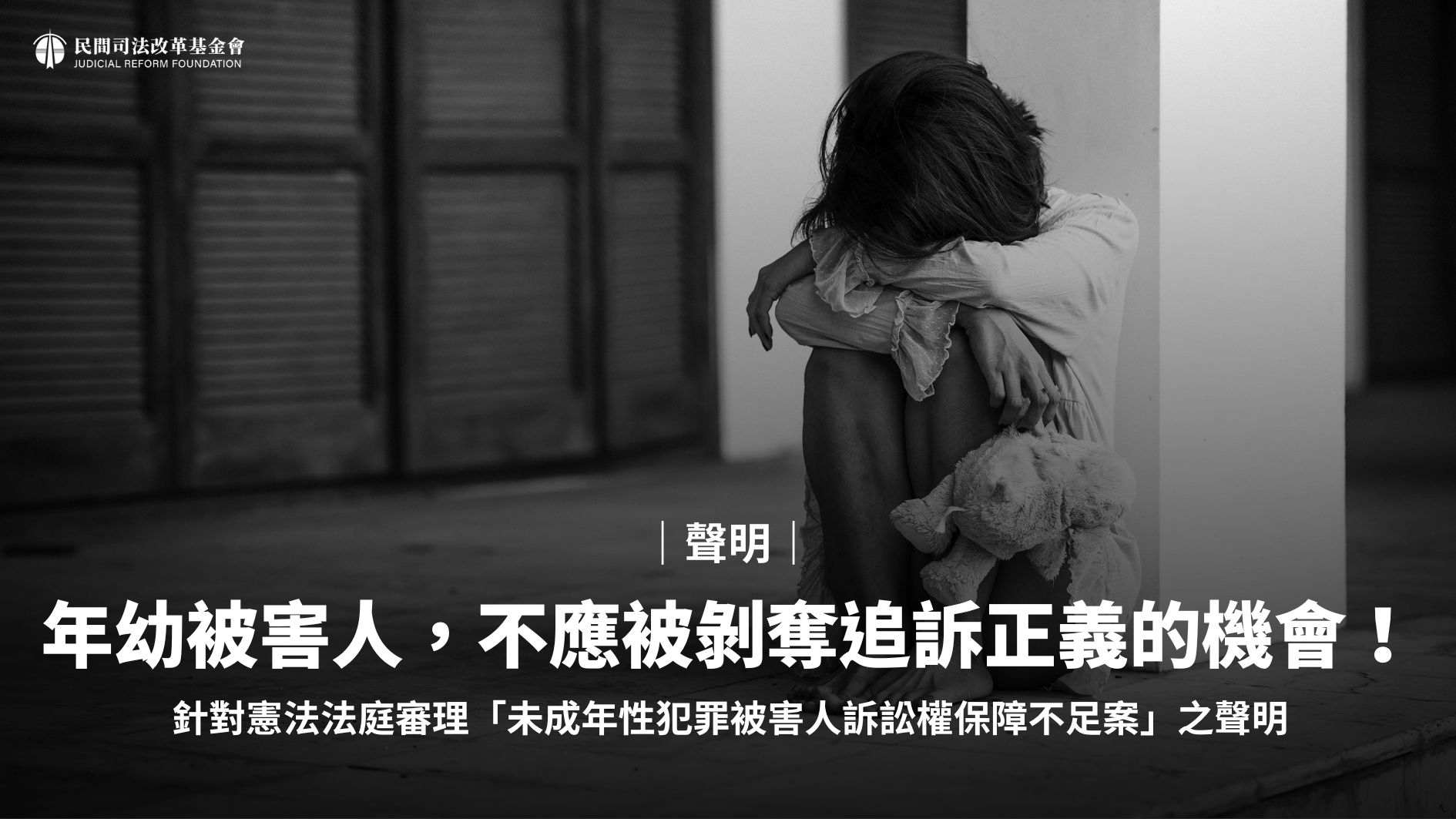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2024年3月20日,憲法法庭受理了人民主張就妨害性自主案件追訴權時效制度爭議,所涉及的法院裁定及裁定所適用的《刑法》第80條、《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等法規範違憲的憲法訴訟聲請(112年度憲民字第384號)。對此,本會也於同年5月27日,遞交法庭之友意見書。
所謂追訴權時效制度,是針對追訴權經時效消滅的案件,國家不再追訴犯罪加害人;犯罪被害人也不能再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責任。此一制度的法律效果,一方面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保障被告不受國家公權力無窮的追溯;另一方面,卻也同時限制被害人受《憲法》第16條保障的告訴權。因此,追訴權時效的審慎設計及衡平極為重要。
我國現行就「未成年性犯罪被害案件」的追訴權時效規定,在法規範適用上與一般犯罪被害案件毫無二致,忽略了被害案件性質的不同;並未充分考慮被害當下可能面臨的特殊處境,如其年齡、心智狀態、所在環境等客觀限制,而為不同程度的規範設計,恐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更無助於落實國家就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保障。
就此,本會提出2點聲明如下,望「未成年性犯罪被害案件」的特殊性被大家看見,不再讓被害人僅因案發時的年幼而喪失為自己尋求正義的機會與追訴的權利:
- 《刑法》第80條追訴期間規定未考量「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所處之特別弱勢情境,已牴觸《憲法》第16條保障之訴訟權。
- 立法院及修法主則機關因盡速修正我國刑事追訴權時效制度,落實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保護。同時,應考慮到被害人進行民事求償的類似困境。
一、《刑法》第80條追訴期間規定未考量「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所處的特別弱勢情境,應已牴觸《憲法》第16條保障之訴訟權:
(一)未成年被害人提出刑事告訴的權利,應受《憲法》第16條保障
《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而訴訟權保障的核心則在於保障受害者能夠於權利遭受侵害時,尋求司法救濟,並獲得公平審判。故被害人提出刑事告訴、追究加害人刑事責任的權利,應受《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然而,現行《刑法》第80條關於追訴權時效的規定,卻並未充分考量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可能因其年齡、心理狀態、與加害者具監督支配關係或其他環境因素而難以行使告訴權的情形,忽略了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可能面臨的特殊處境,而一律以「行為人」之「犯罪成立時」起算訴追時效,顯然對於年幼的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保護不足及產生明顯不公的情況,侵害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提出告訴的權利。
(二)利用未成年人多重弱勢處境的性犯罪,具有特別重大的惡性
參考衛生福利部2022年公布的〈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年齡與兩造關係交叉統計〉,當年度的8,401位被害人中,有4,809位(57.24%)是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在未成年被害人中,每100位被害人,就有16位是未滿12歲的兒童。
統計也進一步顯示,在這些未成年兒童、青少年被害人中,加害人及被害人雙方關係為「家庭成員」者均不在少數,並以「直系親屬」佔比最重。由此可見,這些遭受家內性侵的犯罪被害人並非少數,且處於各種弱勢情境的交疊。
現代婦女基金會也曾於2023年4月17日公布「性暴力事件求助態度網路調查」,指出有高達90%的性暴力被害者不敢報警,40%從未對外求助。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瞭解除上述有通報的案件外,未通報的犯罪黑數甚至可能遠高於上開統計。
不同於一般犯罪被害案件,未成年性犯罪被害案件的特殊性,在於對未成年人為性犯罪者,有極高比例是惡意針對未成年人身心未臻健全發展的特性,利用其欠缺自我保護的意識,以及對性行為、性侵害事實的認知欠缺而犯罪,具有特別重大的惡性。
又縱使行為發生當下被害人確實具備前述相關認知與意識,也往往因遭受性犯罪而產生嚴重身心創傷及負面影響,我們如何能夠期待年幼懵懂的被害人快速走出傷痛,即刻捍衛自身權益?並且,若在犯罪行為人具有「親屬身分」情形下,將使被害人極易礙於家族名譽或其他家人的感受;或出於對行為人經濟上、照顧上的依賴;或迫於行為人的權勢及權力不對等考量因素,放棄對外求助或追訴的機會,根本無法期待他們能夠及時求助或提起訴訟追訴犯罪。
(三)現行的「追訴權時效」制度,令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無從伸張正義
2018年,高雄光華國小體操隊教練梁梅宗,在十多年前長期性侵女學生一案,檢警獲報調查後,發現至少7位女學生受害,當中有4人提告;然而追訴期尚未屆至的,僅有2位。2023年,知名謝姓藝術家遭指控多次對未成年少女性侵,卻因該案追訴期已過,無從究責,而獲不起訴處分,被害人接續提起自訴,仍因追訴期間已過而經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裁定駁回。而這些案件也只佔冰山一角。
我國現行《刑法》第80條的規範設計,並未考量到未成年被害人不同於擁有相對完整的自我保護意識以及對於性自主權遭受侵害的健全認知的成年人,而未給予未成年被害人一定期間的緩衝追訴規範,使其追訴期間規定與一般成年犯罪被害案件毫無二致,無異於苛求年幼的被害人,應與一般成年被害人相同,具備健全的性自主認知及維權意識;且若該犯罪行為人為被害人的親屬,還必須無畏心理及人際壓力、經濟上的孤立無援,在追訴期間內對於行為人提起追訴,否則,一旦追訴期間屆至,就無法制裁行為人過往的性犯罪行為。
如此規定變相淪為犯罪者的脫法工具,顯失司法正義,也跟司法院釋字第664號及第805號解釋理由書,所揭示國家應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權利意旨背道而馳,不但剝奪未成年犯罪被害人尋求正義的機會,《刑法》第80條如此規範設計更有牴觸《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意旨之虞。
二、修正我國刑事追訴權時效制度,落實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保護:
鑒於未成年人年齡、心智、處於之權勢關係等弱勢處境,其遭性犯罪之刑事案件,於刑事追訴期間上應有予以延長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並亦應有不同程度之保護。我國於刑事訴訟制度上,卻未就對未成年人性犯罪之情形,於追訴權時效制度上予以特別設計。
然而,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立場,就《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另有不同之設計。縱然上述兩部法律性質上屬於行政法規,而不同於先前討論的《刑法》第80條刑事法律規定,但在追訴權時效規定的適用上,具有使被害人保障更為周延的核心意旨,仍不失為一有益的規範設計參考。
具體而言,我國《性騷擾防治法》第14條第2項考量到未成年被害人遭遇性騷擾事件可能因智慮未臻成熟或因權勢關係受監督、照護而未行申訴,為了周全保護性騷擾事件未成年被害人,因此設計「時效自成年後起算」的例外規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1條第1項對未成年被害人校園性別事件(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的申請調查及檢舉,更設有「無追訴期限」的例外規定。
除此之外,在外國立法例上,也不妨對未成年犯罪的類型,有特別延長追訴權時效的情形。
就此可知,針對未成年性犯罪事件,外國法乃至於我國法本身皆早有反省,只是至今仍未就《刑法》第80條追訴權時效制度予以檢討而已。基於相同原因,就未成年性犯罪被害人依《民法》求償等權利,也有一併檢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