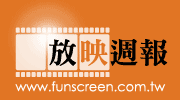採訪整理/王思涵
專題企劃/林文淇、洪健倫、王思涵、王昀燕、禹鐘月 本文由放映週報授權 圖片/張亦惠
現在這個控制是無形的,表面是民主、開放與自由,電視台多了,遙控器轉的平台多了,但它還是受電視台的新聞編輯主控
1980年代,綠色小組面對的是戒嚴很明顯的控制,所以很純粹、直接的需要有我們發聲的管道,我們要有自己的電視台,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我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2014年,一樣被控制,只是現在這個控制是無形的,表面是民主、開放與自由,電視台多了,遙控器轉的平台多了,但它還是受電視台的新聞編輯主控。這才有趣,為什麼相隔30年,需求還是存在?
當時什麼東西不能拍?非官方觀點的都不能,不要說政治,即便是社會的痛苦面都不可以,健康寫實的時代,什麼東西都是欣欣向榮,一切都是好的;社會底層的黑暗面都沒辦法講,像雛妓、原住民勞工被剝削、老兵無法返鄉等問題。
礦災現場的震撼教育
舉個例子,綠色小組還沒成立前,因為我學電影,又在廣告公司工作,有機會借到攝影機,而且我會操作攝影機,我注意到一件事情,為什麼1984年梅山煤礦跟海山煤礦發生那麼大的礦災,電視台只會提礦災發生,多少人罹難,這些人沒有名字、沒有內容、沒有血肉,他們完全沒有畫面,不被看到,這些人好像數字,那時我就拿著攝影機去海山。
那個年代攝影機很少,基本上都是記者才有,所以我進去很容易,如入無人之境。來到礦區的口,煤炭車運上來都是屍體,那個震撼……我是學電影,從來沒看過,只看過美國人拍《礦工的女兒》。屍體運上來一個一個排著,因為發生礦災前剛發薪水,所以礦工是帶著薪水下去的,抬上來的時候,大家要把他們口袋的東西拿出來,就放在屍體上面,幾張鈔票在他胸口或頭旁邊,我是拍電影的人,我知道影像的震撼在哪裡,微薄的薪水,一條命就沒了,親人在隔離線外哭,因為還不能讓他們進去,都是阿美族的。
當時還沒有綠色小組,我沒有發聲的管道,因為認識王智章,我們就說要想辦法這東西弄出去,跟現在很像,但現在有網路啊。後來我們透過黨外立法委員,剪了15 分鐘的影片在立法院辦了一個公聽會,請第一任民進黨黨主席、也是另一位黨外立委江鵬堅幫忙,大家很震撼,但只有自立晚報報導,主流媒體還是不會。
那件事情過後,我們開始醞釀應該要有一個組織。後來陸續追蹤事件,還跑到馬偕醫院訪問家屬,因為有些人沒死卻變成植物人,更慘。(在醫院拍攝時)我們還被警察追,因為第一次有媒體跑到病房訪問家屬,而且我們已經開過公聽會了,他們當然很緊張。
既然需求一直都在,為何綠色小組還是在1990年代解散?
第一,拍得人愈來愈多了,後來綠色常上《自立晚報》與《人間雜誌》等媒體,變成一個重要標的。可是街頭運動不斷,需求量很大,自然有其他團體出來,像是「玉山印象」與「文化台灣」等新的反對運動的媒體,百花爭鳴,這其實還是有市場的問題,因為要賣帶子,看這個錄影帶的人多是關心海外政治的人。
綠色小組在當時沒有什麼偉大的通路啦,只有兩種。第一,找訂戶,跟報紙一樣,綠色小組後來變得很有名,有些訂戶,譬如一個月付五百塊,我們固定提供一支帶子,因為大部分都是支持者,不在乎太貴,對,有點像是粉絲團。第二,很大衝突的帶子就賣很好,像 520 農民運動,噴水,很多人被沖散,很激情,那支帶子大概可以賣到一萬支,而且盜拷一堆,太夯了。印象中,一支帶子是三百塊,批發商是排隊在買,因為那時黨外演講很多,像現在外面很多人賣香腸,都在賣錄影帶,買的人都是一般中產階級的民眾。你看那個多活絡。有時檢總會到製作位置來抄,跟黨外雜誌一樣,只是一個是文字,一個是影像。
書面文字有一種深刻的東西,大家會去看鄭南榕或誰的評論;影像是因為刺激,真實啊,他需要這個東西,電視台看不到,他需要看到真實那一面。
這很有趣,雙方衝突的時候,從台視、華視到中視看到的畫面都是透過鎮暴警察那面看著民眾,就看到民眾在丟石頭,綠色小組等反對運動的媒體都是站在群眾那面,群眾會保護我們,他們會說:「這綠色的!」「這阿堂!」「這自己人啦!(台語)」其他電視台也可以來,只是會冷言冷語說:「這華視的,攏軍方的啦!(台語)」就像現在也會說中天怎樣,一樣的意思,敵我分明。
綠色小組一開始沒什麼章法,就一種熱血沸騰,後來因為市場的考驗,加上不能一直拍同樣的東西,就會開始去設計片頭,例如一個電影開場,也會有主持人,朝那方向走,也因為市場關係,必須滿足新的觀眾,他們不能再看同樣的東西,一直看打來打去,因為衝突就那幾樣,噴水、丟催淚瓦斯啊。
所以電子媒體的出現在反對運動中很重要的是呈現那個衝突的真實、人民的視角?
對,綠色小組真正被那麼重視,兩個元素,一是民眾的觀點,它可以拍到一些民眾的聲音,民眾不是暴民,第二,它可以看到真實衝突的那一面,怎麼樣被沖水、黑道跑進來打人。三台不會拍這個,他拍也只會拍「暴民」,而不會拍黑道介入,三台出現的畫面都是民眾怒,咬著檳榔跟對方罵那個影像,告訴觀眾,都是這種。跟這次媒體去拍喝酒,一模一樣,本質都沒變,所以那個需求還在,驚訝的是說,經歷這麼多年,大家的需求還是一樣,不信任主流媒體,信任自己的觀點,他寧願信任網路上拍得一段,也不會信任一個主流媒體所拍得東西,民眾跟官方中間的鴻溝一直存在,這次真正告知大家訊息的都是學生所拍出來的東西,大家相信這個,即便三立也是,大家頂多去比較這台那台有講到哪裡。
(時代轉變)的基礎在於現在媒材使用方便,會操作這些基本的器材跟使用工具的人愈來愈多,觀念到那個程度,自然會有人使用,傳輸也快。這次的例子很明顯,只要一個iPad,具備操作能力,就能夠把即時訊息傳送出去,就有一個真實。網路世代的年輕人相信靠自己的手機,他已經不習慣坐在家裡跟父母看電視新聞,他寧願看他的同儕拍得東西。很有趣,我自己也是這樣,幾乎不再看電視。
鞏固民主 媒體是指標

鄭文堂導演是當年的綠色小組成員,此次也參與了抗爭運動。
(攝影/洪健倫)
台灣從開放民選總統開始到現在差不多20年,基本上算是新興民主的國家,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鞏固。反服貿會這麼多人站出來,因為感覺民主被破壞。台灣離民主鞏固還有很長的時間,媒體是很重要的指標,現在只是開放,但不優質,所以大家不信任,不能怪民眾。媒體不會自然變優質,一定要壓力,像這次事件就給主流媒體很大的壓力,媒體開放,綠色小組貢獻一部分的力量就是讓媒體至少面對民眾不信任,告訴他們,再不開放,沒有人看三台,都是老觀眾。一樣的問題,即便主流媒體這麼多了,號稱藍綠都有,可是民眾一樣不相信,寧願相信一台iPad,或一個年輕人用手機拍下來的訊息。
現在最大的轉變是東西很短,各式各樣的觀點都有,每個人都發很短的訊息,很短的影像,認真一點的人就從各式各樣很短的觀點找到平衡。綠色小組還是紀錄片的方式,拍再長的東西,人家也看得津津有味,舉例來說,《沒有政府的日子》講李長榮化工偷排廢水造成居民烏腳病的罷工事件,我拍了一百多分鐘,那片賣得還不錯,因為第一次有一記者跑到化工廠的社區那麼久,每天拍阿嬤做手工顧工廠門口,不讓原料進去,我現在看都覺得為什麼拍這麼慢,那個年代只能做那件事,現在不同,那些東西拿來,沒人要看,太長了,其實只要剪成短片就知道全部的故事。
當時是以創作者的觀點講故事,現在則比較個人化?
對,那個年代要操作攝影機即便對警察來說都是專業人士,現在不是,拿著手機,大家都在拍,沒有專業人士的概念,即便你假裝很專業,人家也不覺得你專業。
當每個人都有詮釋發聲權,對運動者推訴求會有影響嗎?會,像現在反服貿運動的狀態比較娛樂化,打卡啊,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美好多元的東西一貼上去,網友夠多就會傳,所以有淺碟化、娛樂化的狀況。是好是壞?我不知道,但是運動比較難聚焦,比如反服貿的策略與目標是什麼?各說各的。
這可能也沒辦法,每個人都有他自主性的論述,我個人是朝好的方向思維,也好,不用那麼民粹,他有他相信那面,他會選擇他的社群、有些人覺得不需要了解太多,只需要了解為什麼不爽,那也很好啊,因為不爽站出來,不一定要了解服貿的條例吧。各種意見都可以,不一定要理性分析,反一個條例就要把它讀清楚,我個人不覺得是這樣。其實這次這麼多人,就一個道理,不爽,以及覺得政府太超過,拜託,今天不是開一個雜貨店,而是一個國家的貿易。
現在網路訊息完全是雪花般的碎片,對參與者的影響比較大,參與意願會受很多枝微末節的東西影響,譬如它在網路上看到三個人貼文說不用去啦,不知道現場在幹嘛,他可能就會受影響;但組織者不會受這麼細膩的東西影響,頂多有件事洗版洗到一個程度,共同討論。
現在的運動組織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我認為本質一樣,但1980年代,組織不多,現在 NGO 小但多如繁星,以前工運農運都跟政黨掛在一起,跟反對黨關係比較密切,大家站在一個同盟,甚至人是流通的,現在政黨不夠好,大家不願意相信,最大的質變在這裡。
變成一個組織才有辦法影響人,讓人家感動,而不是攝影讓人家感動、不是一直在拍人家。攝影可以召喚、可以說明,但就是一個工具,你永遠是一個旁觀者。
組織多如繁星是好的,我還是非常鼓勵年輕人進入群體,成長很快,不管對理念或人際網絡,都很有幫助。我後來加入勞陣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拍人家的痛苦,拍久會無力,想去幫助,放下攝影機,變成一個工運分子,自己下去做,進入組織,所以我有這個性格,我今天的描述也是,變成一個組織才有辦法影響人,讓人家感動,而不是攝影讓人家感動、不是一直在拍人家。攝影可以召喚、可以說明,但就是一個工具,你永遠是一個旁觀者。
坦白說,綠色小組跟反對運動是站在同一陣線,沒有什麼客觀,拍紀錄片是站在工人、農人或資方誰的觀點差很多,一開始就要很清楚:我的顯像站在那邊,沒什麼好逃避。本來,影像就沒有什麼客觀。現在民眾也有各自的觀點,那是一種零散的真實,比較成熟的網路使用者會自己分析,大部分的人沒那麼多時間,看一、兩篇同儕貼的東西就相信了。反服貿運動是這個年代極致的狀態,以後怎麼發展不知道,但所有人使用文字與影像的編輯能力已經到達極端了,每個人是藝術家、觀察家,也是行動指導人。
本期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