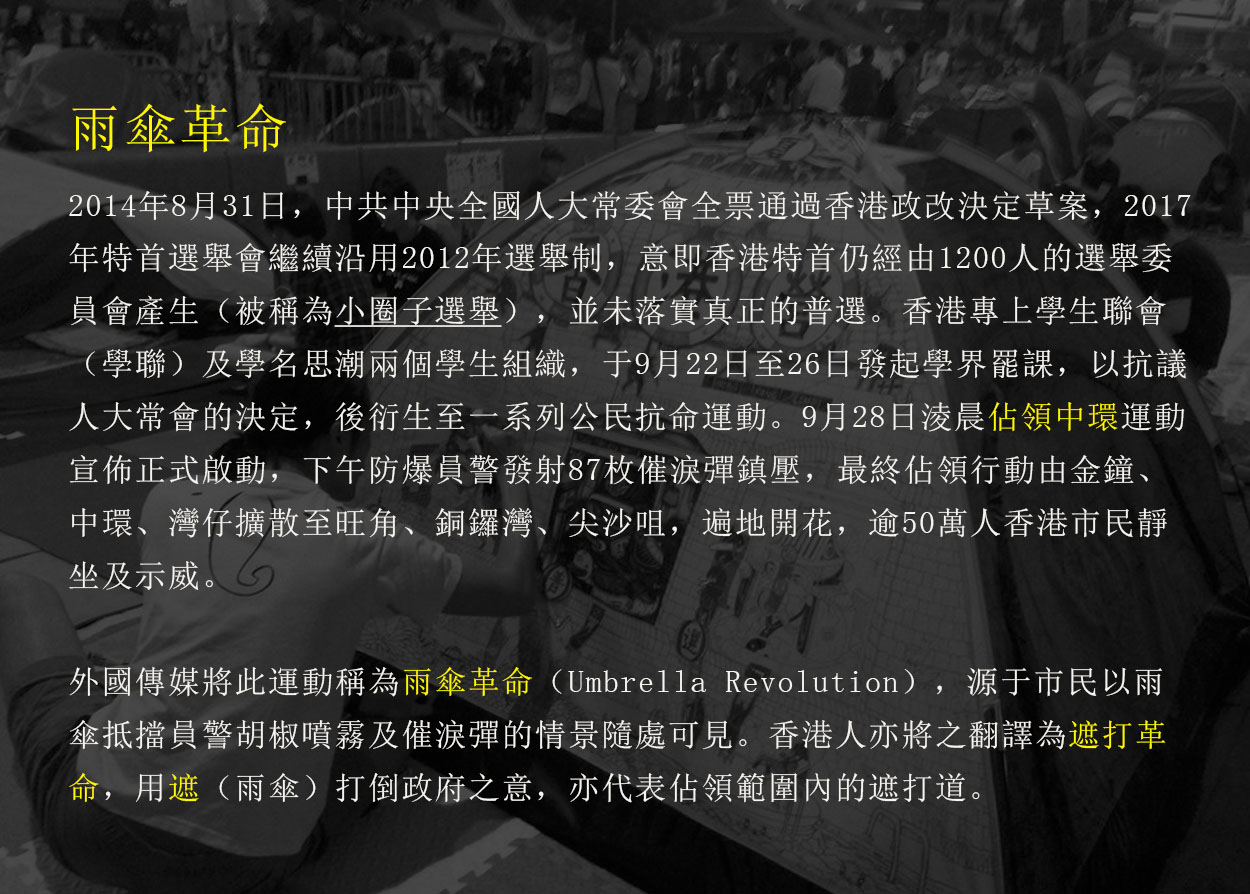文/李雨夢(香港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
重陽節的晚上,在特首辦(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門外,是滿坐在地上的人群,那天早上,員警運送一箱又一箱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明目張膽。又是一個充斥著緊張氣氛的夜晚,不少人戴上頭盔,以免暴力清場再次發生。我們不知道員警會如何對待我們這班手無寸鐵的人,但是幾天之前那87枚的催淚彈,既讓人痛恨員警的濫權,也使人們變得更加堅壯。
才一個轉身,碰到來自《當今大馬》的記者,他特地在放假的日子來到香港,只為見證某個歷史的時刻。我們曾經在馬來西亞有過一面之緣,是在文丁客家村(註1) 村民的記者會上,看到一個個因保衛家園而被員警打至受傷的身體。在香港的特首辦外,一個馬來西亞人,一個香港人,混合著兩種不同口音的廣東話,不斷言說著關於兩地的種種。在他口中得知,馬來西亞在今年多次引用《煽動法令》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和提控,對於言論自由作出嚴厲的打壓,在威權國家的狀況中,彷佛看見了我城的倒影。
7月2日的淩晨,一次預演佔領中環,511人被拘捕。因為反對人大常會對於香港選舉改革的提案,中共一次又一次對於香港普選民主拖延及欺騙,引起學生發出抗議的第一聲。九月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罷課行動,在罷課的尾聲,學生領袖們試圖闖進被拉下鐵閘的公民廣場,這片曾經開放過集會的空間,如今卻是重門深鎖。那個暴烈的晚上,員警把進入公民廣場的學生及市民圍困,並對閘門以外的支持者發射胡椒噴霧,直到天亮, 同時拘捕裡面的示威者,共有74人。首批被捕的包括仍未成年的黃之鋒,這個鋒芒畢露的年輕人,涉及三條罪名:非法集會、擾亂公眾秩序及強行進入政府建築物,在拘留期間不獲保釋,員警更在搜查寓所時候把他的電腦帶走,他的父母斥之為政治迫害,實不為過。馬來西亞有《煽動法令》,我們也有公安條例的惡法。
因抗命而成為命運共同體
9月28日,金鐘的天橋及街道被封鎖,只好沿著灣仔走至演藝學院的那方。那是個天公造美的下午,也是個空氣中彌漫著緊張凝重的日子。從演藝道一直前進,從天橋走到盡頭,映入眼簾的是一整條大道被佔領,朋友說那是會令人流淚的場面。我沒有流淚,但卻充斥著難言的感動,從前社會運動總是小部分的人出來佔領馬路,不用一晚就被員警清走,而當下的香港,公民抗命彷佛真的悄悄栽種在香港人的身上,被催淚彈噴至淚流滿面,卻是去而複返,趕也趕不走。
當晚的形勢非常緊張,不斷收到來自各處的謠言,如十二點後解放軍將進城、員警開槍……加上那些煙霧彌漫的畫面,真的好像打仗般,就連原來答應24小時開放給市民作為避難處的演藝學院,在午夜將近之前亦匆匆把人趕走,就是因為收到警方將會把裡面的人視為暴徒的消息。學聯呼籲群眾離開,但是這夜沒有領袖,留下來的人卻逐漸增多,愈多人愈安全,大家在此刻彷佛都是命運共同體,緊緊相依,互相守護身邊那些認識及不認識的人。
天色漸亮,那晚的謠言一一不攻自破,還發生了佔領旺角的彌敦道和銅鑼灣的軒尼詩道,兩條都是香港交通的重要樞紐,與九龍與港島一脈相承。然後,因為以雨傘遮擋催淚彈而生成的場面,壯觀得成為了一場“雨傘革命”,或是被視為更貼切的“縮骨遮革命”,佔領中環已經退場,而這場運動亦從學生運動轉變成為了全民運動。
據點分散了在金鐘/銅鑼灣及旺角,兩邊的氣氛截然不同;旺角一邊,參與者的成份更為複雜,來自不同的階層及年齡。記得佔領彌敦道的第一個晚上,謠言同樣此起彼落,說是有MK仔(註2) /紋身漢在鬧事,消息混亂,但總算是“平安”地度過了那個晚上。
兩條平行線的有感與無感
第二天早上,因為某些行政事務上的必須,特地回了一趟嶺南大學,即使學聯沒有宣佈無限期罷課,大家都是沒有心情繼續上學。看到聚集於學校永安廣場的學生,臉色上的急切,都渴望為這場運動提供一點力所能及的協助。
那天我因回校而坐了兩程西鐵(捷運),來回往返,我遇上了兩對截然不同的人。
第一程,旁邊坐著一個操著非純正廣東話腔調的疑似新移民婦女,帶著六、七歲的兒子,我們都在看鐵路裡頭那小型的電視框,人小鬼大的小孩脫口而出︰“員警怎麼可以如此暴力對學生!?”身旁的母親認同孩子的話,有些感慨地說出同一番話︰“對啊,員警怎麼可以如此暴力對學生。”雖然我心想被暴力對待的,又豈止是學生?然而,我這兩天比較眼淺,聽罷鼻來一酸。
回程,身邊坐著中產打扮的中年男子,在我耳邊,強迫我聽了他講十分鐘的電話。滿口自以為是的說話,說起兒子昨晚不回家但只說是去社區中心都被他罵,女兒好像是學生會的人,也被他警告了一下;又說自己並不相信什麼價值,只相信真相(媽的,真相不就是員警不斷向群眾投放催淚彈,以不合理的武力對待手無寸鐵且和平到不行的人嗎?),再不斷講講講講講,那十分鐘,我真心覺得他對我造成了滋擾,致使我無心專心看書。那一口流利的廣東話,真的比髒話更難聽。
街頭上庶民的多樣與混雜
再次來到旺角街頭,沿著太子區走到油麻地方向,還是充斥著滿腔的感動。在平常日子的狀態中,我很討厭到旺角這個熱鬧地區,人多擠迫,本地人與自由行的混合,讓人喘不過氣。但是被佔領之後的旺角變得再不一樣,甚至可以鬆動人們對於街道這個公共空間的想像,場域性質的轉換,更加貼身地感受得到。
有人警惕不要過於鬆懈,員警消失、滲透可能引起的混亂效果,這些我通通都懂,亦能理解。但我還是很喜歡旺角,庶民的多樣性在此處開展,一個全民的運動,裡面參與的人本身成份就非常斑駁及混雜,重要的不是排斥(滲透的人當然另計),而是如何與這些看似難以溝通的人進行溝通,還有嘗試互相理解。
在現場遇到舊同學,他說看到去年認識的幾個碼頭工人(註︰2013年3至5月葵青貨櫃碼頭爆發嚴重工潮)都來到彌敦道支持,讓我深深感受到那是運動組織者在過去所種下的種子在發芽。我想,思考多一點如何去互動,總比散播流言來得更實際。
旺角的平靜氣氛延續數天,直到一群反占中人士及黑社會的出現而發生嚴重衝突,他們打人、非禮女生,然而員警在場卻沒有盡職,非到了現場人士起哄才拘捕肇事的人,卻又被人發現在另一邊廂把拘捕的人放走。員警的所作所為,雖聽說有嘗試保護在場的佔領人士,但還是不禁令人倒抽一口涼氣,一個星期前才佈滿警力甚至出動防暴員警及催淚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反對聲音,為何待遇的差別竟是如此誇張地不同。一直對於員警沒有特別的憎恨與喜愛,心知肚明他們作為國家機器的一方,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但是,比起87枚催淚彈,我更無法接受警方的選擇性執法,這是完全超越底線的私相授受。
期望光明權利的螢螢微光
毛澤東說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這場運動的局勢中,甚至連朝夕都太長,似是天天都在變化,還未好好消化就已經有下一波的局面,而這種緊張,也包括了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攻訐太容易發生,在撤離與留守之間亦出現極大的分歧與爭論,運動出現的去中心化沒有單一意見領袖,這是好事,但如何組織起來是參與者需要面對且思考的一道大難題。
執筆之時,正值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108歲誕辰,我在佔領的旺角街頭中看過有人貼起印著她頭像的宣傳單張,粗略地闡釋了她最為著名的“平庸之惡”這個概念。然而,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曾經寫過這段話︰“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
祝福我所愛的城市。
寫於 香港 2014年10月14日
- 註1: 2013年10月,百年文丁客家村十多戶屋子遭發展商強行拆除。村民組織並發起保村運動。
- 註2: 由於旺角以前是柴米油鹽衣物等貨物的集散地,因此成為黑社會派系必爭的“油水區”。當中年青一輩為突顯自己身分,會在外型與身體上作出與眾不同的打扮,這些人經常被稱為“MK仔”(旺角Mong Kok),後此裝扮成為許多年輕人模仿的潮流文化,加上旺角有許多針對年青人的娛樂與潮流服飾消費場所,該名詞也泛指經常出現在旺角的年青人,象徵某種香港道地旺角文化的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