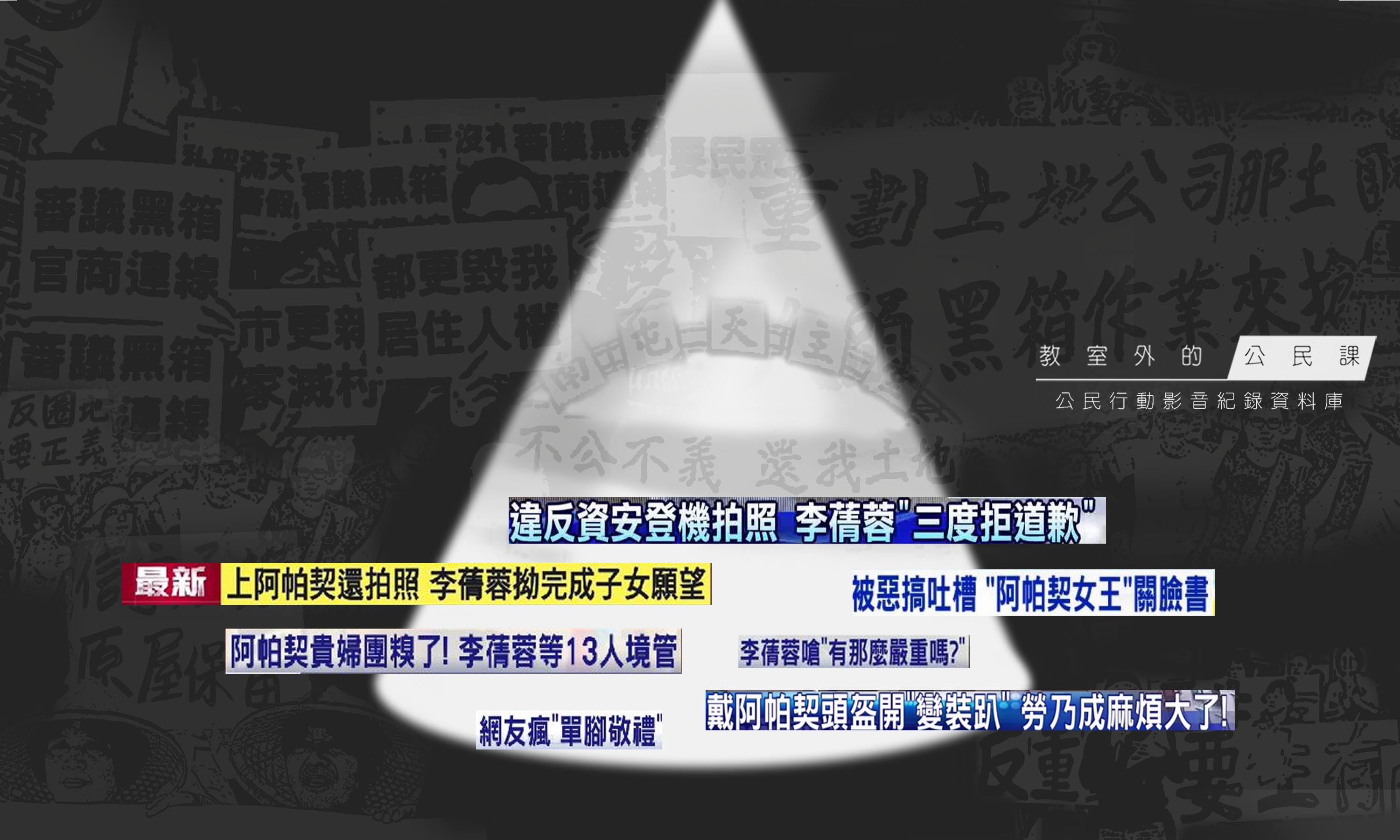文/鍾明倫(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近來,發生的阿帕契事件已經使得全民瘋狂,不論是相關與不相關的公眾人物都可以參與阿帕契事件的論述,媒體的焦點集中在李姓藝人與勞姓中校的法律與道德責任,也開始瘋狂地對於當事者權貴背景進行徹底的檢視與批判,並且把「權貴的身份」與「違法濫權」劃上等號。集體社會對於權貴濫權的批判是成熟的民主態度嗎?啟動集體社會審判的機制是什麼?筆者透過阿帕契事件反思「媒體集體崇拜」的基本形式,以及邁向神聖社會(理想公民社會)的迷失:
第一、該事件已經進入司法調查,媒體每天透過密集的報導帶領社會審判違法的藝人與高級軍官,這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的監督原則?若今天違法的不是「權貴家族」,而是一般無權無勢「老百姓」,那麼這個社會仍然會繼續以同樣的標準評價這件事嗎?再者,人權團體是否需要為權貴家族捍衛「無罪推定的原則」? 是否需要捍衛審判的「程序正義原則」?面對不同階級的違法犯罪,社會集體性的批判若有不同的法律與道德標準,試問這個社會運作背後的核心價值是什麼?這個集體批判的目的是什麼?
第二、若將該事件的犯法者繩之以法,是否改變了「黨國資本主義」(國家透過權威結構與律法維繫資產階級對於社會的控制)的社會結構?若無法改變惡質的社會結構,試問集體社會的批判與審判究竟是滿足了誰的需要?我們需要質疑的不應只是「誰」該負責,把法律責任「個人化」,更需要質疑的是:推動權貴違法濫權的「社會機制」是什麼?直言之,若這個社會機制沒有被徹底的改變,「懲罰個人的違法行為」是否可以說是一種維繫制度運作的包裝?該事件就如同中世紀的燒女巫(獵巫)運動(即女主角的「巫」名化),將施行巫術的女巫/阿帕契事件的犯罪者帶到宗教/世俗的法庭審判,目的只是想要維繫某個歷史時期社會結構下的宗教/律法的權威,而非改變社會結構與解放人性。
第三、人類的文明不斷的嘗試從宗教的權威解放出來,但是卻忘記了人類也進入世俗的權威當中。因此,人類逐漸凝透過集體性的批判行動凝聚情感,達到世俗化的神聖社會的狀態(理想的公民社會)。媒體的「獵巫活動」與社會的「集體審判」不就是推動人們邁向神聖的社會,使人類繼續相信理想社會的「權威結構」,即:「法律可以保護善良的公民,懲罰違法的公民」或「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政治想像。然而,這樣的想像使人民享受在集體批判的歡愉當中。換言之,每個人透過批判權貴的行為似乎成為正義的使者,但卻麻木於社會的權威結構之下,更使得人民依賴律法,卻忘記了台灣社會結構是黨國資本主義的產物,即:一批權貴離開,將有另一批權貴取而代之。
第四、解嚴之後,隨著民主與政黨政治的發展,台灣的社會結構逐漸從政治社會逐漸走向公民社會,媒體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監督角色,也被稱為第四權;相對來說,台灣的媒體商業化發展也似乎帶領人民進入黨國資本主義的公民社會,並將集體的批判視為通向理想神聖社會的道路,媒體的「即時爆料」不僅落實「媒體近用權」的理念,也讓每位公民成為「監控者」與「被監控者」,當有人提出新的爆料資訊,整個社會卻響起一片的掌聲,並為之瘋狂,這也更加深人民對於媒體的集體崇拜與依賴,這樣的邏輯或許就是現代公民對於媒體崇拜的基本形式。批判來說,整個社會從阿帕契事件得到的反省是什麼?集體的獵巫行為與集體的審判改變了什麼?如果都沒有改變什麼,那我們和那些高喊燒女巫的中世紀人民有什麼不同的呢?
第五、當阿帕契事件結束後,將會有新的事件取而代之,媒體也將繼續引導閱聽者在新的議題繼續參與公共論述,這樣周而復始的批判與監控/被監控真的讓我們更接近理想的民主生活嗎?辯證來說,公民透過媒體展性理性的一面,相信批判帶領我們通向美好的社會,但是,閱聽者可能只是陷入媒體崇拜的理性牢籠中而無法自拔。總而言之,集體理性的展現若只是停留在審判個人的違法/偏差行為,而非徹底改變與翻轉黨國資本主義的結構,那「社會集體批判」是否表徵另外一種「社會集體崇拜」的形式,不切實際地想像著美好「神聖社會」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