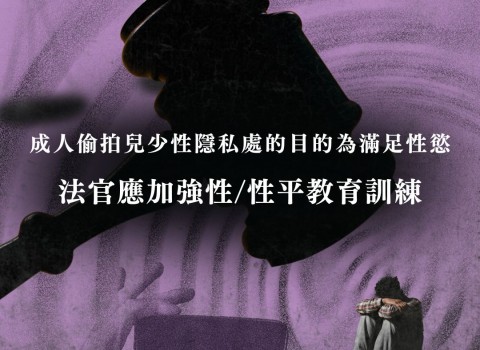製圖/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文/黃亦宏(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研究生)
保二總隊男警葉繼元因欲留長髮違反《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務重點要求事項規定》,累積二十支申誡,經保二總隊召開考績會後決議予以免職處分。
對此,前警大教授、現任警政署性別平等委員葉毓蘭認為:「警察為特殊行業,必須要有威儀,讓人民信賴。」葉毓蘭說的特殊行業的意思,即主張行政法學中的「特別權力關係」,意即相對人的身分與國家有特殊關係,故其法律權益受特別限制,國家在一定範圍內對相對人有概括強制命令之權利,相對人則有服從義務;如人民處於特別權力關係,因其承受較一般人民為多的服從義務,因此從人民角度觀之,亦可稱為特殊服從關係。
我認為必須重新商榷以「特別權力關係」主張男警不得蓄髮的合理性;下文我先從「特殊」談起,再談「特別權力關係」。
事實上,蓄髮特殊與否並非固置的本質,而是透過法律、社會文化建構出的思考框架。回看台灣刑法中的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六條第四項衍生出的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第三條「少年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少年不良行為」,第三條第十四項「穿著奇裝異服、儀容不整或男性蓄髮過長」。這也就是說,在1999年修法前的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認為男性少年蓄髮過長是一不良行為,有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警察機關可視情節處理,對於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之預防…必要時,並得洽請憲兵單位參加。
若以現在的眼光回看,可能會覺得當年認為男性少年蓄髮有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荒謬可譏,然而1972年立法的社會環境與政治氛圍,有其「特殊」之處。1971年台灣宣布退出聯合國,外交情勢慘烈、接連喪失邦交國,國內蔣氏政權逐漸遭受挑戰,在此一時期以法律處罰深具反抗家長、國家權威意味的蓄髮少年,從小地方宣示國家的控制權力有助於維穩政權,懲罰少年的反叛心態以提升對社會秩序的控制(第三條第十六項「使用暗語怪號交談,行為詭秘。」更符合這個推論)。
1999年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修法,刪除服裝儀容與蓄髮規定,修法有其複雜的歷史脈絡在此不便長論;但修法刪除蓄髮規定顯示國家不再認為少年蓄髮有害於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或至少不再以此法管制),因此蓄髮影響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與否並非一固置不變的本質,而是與該法施行的時空環境有關,也就是說,權力者為達其特定目的而透過論述建構特殊性。以法律限制可否蓄髮有其特定的社會控制意義,反應的不僅是表面上維護善良風俗或社會觀感,更是上層權力機關施加、強化思想、行為管控的方法之一。
上文我已說明特殊與否是特定時空、論述的產物並有其社會控制意義,而警察工作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則與其作為國家權力的執法者有關(特別權力關係)。在討論特別權力關係時,我認為應分為三個層次來討論,第一、主張特別權力關係是否合理?第二、特別權力關係的限制是否合理?第三、特別權力關係的限制有性別差別待遇是否合理?
關於第一個問題,前司法院大法官許宗力在釋字653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認為我國早於民初就已引進特別權力關係,施行迄今,但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未見諸憲法明文,習慣法說是特別權力關係最有可能的立論依據(但習慣法可否無視憲法第十六條及二十三條明文相違)…特別權力關係自引進之初便以教條姿態出現毫無說理,就悍然以教條之姿剝奪人民基本權利。
許宗力在該文中質疑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依據並分析其違憲疑慮,經司法院解釋多次努力作成的若干突破,他認為可以向特別權力關係說再見了。然,我不打算繼續深究特別權力關係是否應受全面揚棄?若在這個問題上打轉,恐怕無法與主張特別權力關係者對話,我想從承認特別權力關係開始,談限制是否合理?
有關大法官曾就特別權力關係做出多號解釋,比如釋字187號、243號、298號、323號、338號、382號、395號、430號以及653號解釋等等,皆對特別權力關係形成的限制有所討論,從大法官解釋調整特別權力關係的限制來看,顯見特別權力關係的限制界線是可經調整而非固定不變。故,即便同意警察與國家之間有特別權力關係,在此一事件上仍然可以提問,針對髮長有所限制是否合理?
然而髮長限制是否合理的問題會直接滑向髮長限制有性別差別待遇是否合理?原因在於若我們查看《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務重點要求事項》,不難發現,除第一條第一項特別針對性別有不同規定外,第一條從第二項到十三項、第二條(共十二項)及第三條(共八項)並無其他性別差別要求,可見髮長限制是基於性別而針對男女警有不同規定。因此,髮長限制是否合理的問題,其實是限制男警蓄長髮是否合理?
針對限制男警蓄長髮是性別問題的主張有幾種流行的回應,我在此稍舉幾個常見的限制男警蓄髮的理由,試論其背景因素其實是性別問題而非其自身:
第一、維護警員形象: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林麗珊,提出警政署統計處2014年的調查報告,指出有66.17%的民眾仍不太能接受制服男警留長髮,這呼應了葉毓蘭回應此一事件時認為「警察為特殊行業,必須要有威儀,讓人民信賴」;然而這樣的說法以及民調,事實上僅是重製性別刻板印象。這句話的意思即為男警蓄長髮沒有威儀使人民不信賴之,這也是許多民眾反對男警蓄長髮的主因;然而此種認為男生必須要有男生樣(短髮─陽剛─藍色─機器人)女生必須要有女生樣(長髮─陰柔─粉紅色─芭比娃娃)的性別刻板印象,正是過去幾十年來,婦女運動以及性別研究亟欲破除的性別壓迫。這也就是說,即便當前的社會氛圍確實認為男警留長髮並不適當,有害於(性別)公共秩序,那也僅表示,台灣社會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壓迫現象習以為常、對性別表現有深刻的刻板印象,乃至於現存的性別結構遭挑戰時,大眾無能思考性別結構如何控制性別表現打壓性別不從者,甚至極力維護現有的壓迫結構。
第二、紀律問題
名嘴黃暐瀚認為警察,是一個紀律的團隊,全台灣七萬多名警察,都依從著一樣的規定…其實問題並不在葉繼元的長髮上,而是在於他持續的「不服紀律」。黃暐瀚沒能理解「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務重點要求事項」針對男女警的髮式有不同規定,即反映出在制定相關規定時,制定者就已依傳統性別想像,制定男女警不同髮式標準之規定。因此,若以紀律問題論之,不可跳過髮式規定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性別想像,制定者的性別刻板印象導致其將男警蓄長髮特殊化,將之建構為須受限制的紀律問題,這也就是說,男警蓄長髮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特殊的論述建構。由此觀之,男警蓄長髮有害於紀律,其實仍是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
第三、便於執行勤務:
「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務重點要求事項」針對男女警的髮式有不同規定,其中女警可蓄長髮而男警則否,據此,若主張限制男警蓄長髮之理據為便於執行勤務,論者應證明男警蓄長髮對於警察工作的執行確實有害,並且女警蓄長髮無害於工作執行,因此女警可蓄長髮而男警則否,如此才具限制男警蓄髮的性別限制正當性。若無明確事例佐證蓄髮對不同性別的警察執行勤務工作確實有異,那麼,值勤問題便是假議題,男警不得蓄髮又回到性別問題。
本文試圖從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管理辦法,說明其對蓄髮過長的管制是透過立法將蓄髮建構為須受管理的特殊行為,而後的取消顯見蓄髮影響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其實是被建構的思考框架,男警的蓄髮問題也同樣的是經論述建構出的特殊問題;關於特別權力關係的主張,從大法官解釋不斷放寬特殊限制來看,不難發現,即使身處特別權力關係,其限制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經時代改變而調整或取消限制的,因此,除非論者能夠提出適切理由限制男警蓄髮,否則特別權力關係也不應成為限制男警蓄髮之理由;而針對男警不得蓄髮的形象問題、紀律問題、值勤問題,我已一一指出其背後的限制理由,其實都是性別問題。綜上所論,面對男警不得蓄髮的質疑,論者應回應限制的正當性問題,若無適切的正當性僅因性別而設限制,我認為應撤回對葉繼元的免職處分並取消男警的髮長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