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廖福源(社會工作者)
首先釐清,王姓兇嫌有沒有精神疾病尚未釐清,就算有,其與殺人行為亦不見得有關連,也就是說,他仍可能是因精神疾病以外的原因殺人。
內湖女童遇害後,衛福部心口司表示將放寬強制就醫的規定,此舉在時光倒退後真的就能阻止這起不幸事件的發生嗎?或者是適得其反的引起更多的問題?曾任衛生署精神衛生法研修委員的政大法學院副教授劉宏恩近日於受訪時指出,96年精神衛生法修法前,「強制住院」因為是「依法」為之、「政府公費全額補助」,病人住越久醫院就可以賺越多。另一方面,僅需兩位醫師同意即可強制住院,在當時還曾發生過「同性戀被家人強制送醫」的案子,至於沒有精神病的街友、遊民被強制送醫的案例則又更多。
目前許多的討論中,「強制就醫」的議題持續在「疑似精神病人」的人權,以及「家屬」人權之間擺盪、消長:病人就醫了,家屬喘一口氣;病人人權得伸張,回到家後,家屬皮皮挫(台語)。強制就醫變成是人權之間的拉鋸戰,可是其中的困難被治療了嗎?被解決了嗎?這其中的難處,可分別以「強制」和「就醫、治療」兩個面向闡述之。
強制要件界定的困難
筆者在社區服務精神障礙者已逾八年,我曾經強制就醫過一名服務對象,當時如此判斷並不是因為他有嚴重的攻擊行為,而是他利用情感關係、製造恐懼將太太關在家不讓出門。由於沒有明顯自傷傷人行為,當時我也評估其可能會被醫院退件,所以也在過程中不斷地搜尋精神醫療的疾病診斷的方式、事情的嚴重程度,向警消、醫護人員說明。同時又要跟服務對象溝通,試著讓他不那麼抗拒,並且知道為什麼他現在需要住院治療。

老實說,以我社工專業背景,處理強制就醫已備感艱難,可以想像非專業人員的家屬在過程當中的困難。蓋強制就醫須符合嚴重病人定義。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項指出:「『嚴重病人』是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在情況焦急時,家屬往往說出的是困擾、擔心害怕及難過的心情,這時精障者的表現通常會識時務地變得很冷靜平順,家屬的情緒恐怕還大於精障者,以致於無法協助醫師能準確的判斷究竟符不符合強制就醫的規定,然而潛在需求者無法強制就醫,回到家中又是家庭要承擔,前幾年桃竹苗地區就曾經發生強制就醫未成功,結果回到家開瓦斯自殺三合院爆炸的悲劇。
「治療」成效的困難
即使強制就醫成功了又如何?精神衛生法第42條:強制住院期間,不得逾六十日。回到關於治療本身及住院環境觀之,以目前的精神醫療,有些病人在住院後的確得到緩解,卻也不乏許多撐過60天,準備回家找家人麻煩的案例。現在的精神醫療雖明確指出發病原因包含了生理、心理、社會因素,可是在住院期間往往只處理了生理因素,用大量高劑量藥物去壓制急性病人,卻花很少的時間及人力去關心究竟精障者發生了什麼事、遭遇了什麼,加以住院環境又非常封閉跟外界隔絕,因此住院過後,往往帶著許多對醫院及家庭的不滿而回到家中,接續著可能是週而復始、千篇一律的惡性循環。
以我自身的另一個經驗,原本一位我曾經數度帶他去職場就業、跟我信賴關係不錯,什麼都能談的夥伴,在執行強制就醫後關係破裂,甚至惡言相向,更何況是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必須時時面對的家屬,那樣緊張的關係,又是多麼地令人難受!曾經有家屬說:我再也不想把自己的家人送去關,覺得對不起他;也有家屬說:把他強制就醫時我能喘一下,但出來之後我們家就糟糕了!
社會大眾對這些家庭的苦痛與困難,往往難以理解,甚或衍生許多誤解、指責:認為凶嫌家庭應該負責、認為家屬要連座、家庭責無旁貸。這些話聽起來高高在上、很有道理,卻不知現在家庭在社會支持的破洞裡頭遭遇的困難!醫療失靈、社會支持系統失靈,卻要求家庭獨力承擔!
問題現況
1. 精神醫療重視生理、輕心理社會
就醫治療期間,偏重生理的精神藥物治療,缺乏心理社會層面的幫助,精障者在醫院的治療過程,只有處理生理狀況,但沒有療癒心理社會的需求,以致於帶著更多積壓的情緒出院。心理師在健保體系下做的則是比較符合健保點數的心理衡鑑,更重要的心理治療不被重視,台灣精神醫療重生理、輕心理社會,也反映在資源大量投入醫院,輕忽社區支持網絡。
2. 出院準備計劃未落實
病人出院準備計劃沒有落實,無法和出院後的社區聯結:我們曾經在不同場合、時間問過家屬及精障者知不知道出院準備計劃,大部份的人說不知道,有些人說聽過但沒有用。這是護理人員的工作,可是在護理勞動條件如此惡劣的狀況下,實在不忍苛責,筆者也認為這不是單他們就能扛起來的。出院準備計劃應該由醫院團隊、社區團隊、精障者、家庭共同召開會議,讓住院期間的努力得以延續到社區的復健、就業準備到返回職場工作,可是以現行實際的狀況是:出院準備計劃未能落實,醫院與社區接連是有斷層的。
3. 家屬缺乏支持
要家屬負起照顧責任,但誰來支持家屬?精障者出院後還是家屬承擔,誰來幫忙?資源在哪裡?是否足夠?以首善之都的臺北市來看,資源仍是遠遠不足,報導指出,北市列管精障人口1.8萬人 照護員僅200人。其中關懷訪視員事實上也只是一區一名,一個月案量30至50名,以這樣的案量一名精障者一個月至多訪視一次,何來服務品質!與精神障礙者的工作基礎是關係的累積,一個陌生人一個月來家裡一次,就算沒有感到莫名其妙而拒絕受訪,一個月一次又能支持到什麼?再者,種種原因導致關懷訪視員流動率大,而多數的公共衛生護士其實跟精障者接觸多半是兼辦業務(可能只是業務十分之一),又常會轉換業務,如何長期支持陪伴精障者及家庭呢?另一方面,家屬本身也需要資源及支持,可是實際狀況常是我們把快耗竭的家屬當做是個案管理的資源,而看不見家屬/家庭也是需要資源及支持的對象。
4.精神疾病汙名化
筆者去年才協助一名大學畢業的精障者到社區工作。畢業後他找工作受挫,跟我說:年底找不到工作他就不想活了(家庭背景非常辛苦),所以當他面試到一份工作後,因細故要找人擔保切結,冒著各風險我硬是幫忙簽下切結書,可是不久後,該單位的承辦窗口說擔心他有精神疾病壓力太大,不是那麼適合這份工作,他再度受挫。幾年前也有數家康復之家,像是基隆深美康復之家,也遭受居民的抗爭多年。我也曾寫下我的家庭故事,可參我的大舅舅。

精神障礙者返回社會的路迢迢(許多犯過錯的人也是),前方沒有希望,社會不支持還會歧視,最近的新聞讓服務對象說:社會大眾這樣說我們,會讓我們更不敢去看醫生、走在街上,不知道要怎麼去面對社會了。對照之前台大生情殺案,我們會討論的是台灣教育怎麼了,可是這次事件一出來,卻說要監管精神疾患?
關於前述問題,建議如下
1.以精神疾病經驗者的生活層次來看,要從社區照顧連接到社區發展的支持服務:
精神疾病經驗者的狀態有高有低,以功能性來看也跟其他障別不同,功能高低隨著服藥穩定性、生活規律、復健狀況、就業穩定甚至是幸福感而有很大的變化。因此社區所提供的服務層次需要很多元,不只是以重度或輕度為分類,因為有的重度精障者也可以去就業,而不是住到慢性療養院。
以會所模式(clubhouse)為例,就俱備社區照顧以及發展支持的功能,可以讓有些較重度障礙者也能參與社區活動,有較多的人際互動設計,不是單純的照顧取向。會特別提出不能單純照顧的原因,乃來自於精神疾病經驗的經驗上的特殊性,他們可能即使重度也會有思緒清楚的人,他們接受完整的教育、曾經有謀生就業能力、甚至是豐富的人際情感需要,只是因為精神疾病後的經驗重擊而被醫生及社會判定重度,所以在社區照顧上不能只偏向照顧取向。龍應一個角度看,他們因為擁有好的認知及感覺所以更能感受到疾病的痛苦。
而其他輕度或中度的朋友(其實我認為沒什麼程度差別)更是有多層次的需要,因此一個單位要發展足夠多元的工作,特別是社群的組織,在會所(社區)裡最重要的就是豐富性、延續性(不以人的生命發展歷程及階段做切割,而是提供長期甚至是永久的支持,同時有就業就學復健訓練陪伴)及社群關係了(工作者與精障者是夥伴關係,而且去病),而我在當中工作幾年後,看見其中社區工作發展的芽,意思是怎麼讓單位組織與社區共同發展的關係,讓社福單位不只是社福,而是社會公眾健康的組織,精障者不只是病人,而是真正的社會公民並且是倡議者,因此我們持續在推動會所模式進入社區的各個角落(會所其實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但對目前精障領域的發展是相對好的土壤)。
至於特別談到社區發展,是為了面對社會集體對瘋子的恐懼汙名,同時將問題意識層次拉到整體社會來看。社區發展要先有一群有共同生活經驗的人,有共識、有共同目標,彼此一起工作,在各個層面協作中去磨合關係及生活政治經驗,會所的夥伴關係及社群組織其實就是在培力這個部份,而後有條件有能力共同去面對社會的不瞭解、歧視、壓迫,所以會所(或任何有此意識的單位)得先從最小的單位(里、企業、社區協會)開始發展跟社區的關係,精神疾病經驗者或社區有機會有了新的實際的互動經驗,重新互相認識彼此,而帶來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2.落實出院準備計劃,讓醫院、社區得以連接
醫療團隊必須一起跟社區團隊、家屬、精障者溝通,建構、連接他們出院後的資源地圖及社區景況,這不能由單一方面決定,否則就會變成我前述精障者出院後爆炸、怨懟以及社區沒有相應的人承接,最後還是個人及家庭承擔
3.強制就醫外的另一種選擇:在社區短期治療及居住的住所
強制就醫被退件了怎麼辦?照顧者與精障者發生衝突了,該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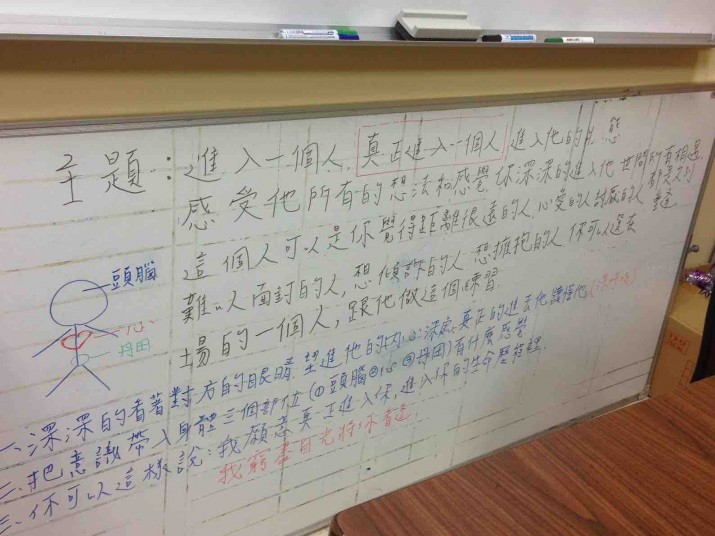
有時他們不是發病了,而是人際間衝突,但被送到了醫院,接著所有的認知、情緒及行為被疾病化,以症狀解釋,於是住院加藥,副作用一堆,又要重新復健,又進入一個治療的旋轉門(如同生活狀態的旋轉門),其實真正原因可能是個誤會或尚不能理解的經驗,加藥調藥只不過息事寧人,何況,這又有強制就醫的複雜性,有些新聞不就是被醫院退件了嗎?如果有一個專門面對特定狀況,短期居住調整的地方,可以拉出一個有界限的空間讓關係澄清,相互整理發生了什麼;有些被醫院退件,其實是在於住院品質本身很不好,精障者不喜歡在醫院的感覺,因此不願意住院,但如果那個地方像是個家,相對自由,又有協助治療的人員,會不會因此改變想法呢?當作去住別人家呀!
國外範例一:Soteria house
Soteria是一個社區服務,為人們經歷精神痛苦或危機的中繼空間。 Soteria往往被視為藥物、醫院系統之外的溫和替代品,提供「早期干預」或「危機處理」的服務。
國外範例二:紐約降落傘危機暫息中心
降落傘危機喘息中心,可以讓人們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休息。當事件、情緒變得過於緊繃,一般正規的途徑就是前急診室或住院設施,在那裡,需求者不上學、不工作,暫時失去社會生活。然而在喘息中心,不僅可以得到照顧,而且還能延續原有的社會生活,始終保持與社會融合,這是一個提供最少干擾的工作模式。
降落傘危機暫息中心的第二個重要特徵是,它們是以同儕運行為主。支持人員都是曾經經歷那些情緒或心理危機的人。工作人員都在康復中,也可以以身示範、分享如何經驗。第三個重要特點是,服務具有連貫性。當需求者回到社區後,仍然可以繼續使用相關資源。過去經驗,行動危機小組曾支持一個曾經經歷危機的對象長達一年。
國外範例三:海爾模式
早在十四世紀的比利時海爾(Geel)用家庭住宅的治療方式,以社區共融的方式來處理社會心理問題這個方式延續了數百年,因將精障病友安置寄養家庭照顧而聞名國際。剛開始因為宗教、慈善動機,社區民眾接納精障病友為家中成員,在專業醫療下協助他們社區復健,並視為榮耀;其中寄養家庭需通過種種資格審核。後來在當地政府經費支持,持續精障病友寄養家庭照顧模式,成為該社區特有文化。Jackie Goldstein(1998)的報告指出該社區在1930年代最鼎盛時約有4000位寄宿病友,隨著寄宿人數下降,截至1998年7月約480個寄養家庭,照顧580位患者。

公庫成員曾到精障機構伊甸基金會的活泉之家分享另類媒體的運作經驗,而活泉之家即採取「開放式對話」與精障者互動。
高雄市政府陳菊市長也在民國97年赴比利時等國考察後,希望「台灣社會也能有此「Geel」精神,提供精障病友更多的溫暖和鼓勵,讓他們儘速恢復健康,有機會回到社會工作,這才是一個進步的健康城市。
4.建構到宅式的精障家庭支持系統計劃:
目前伊甸基金會附設活泉之家與由家屬組成的台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甘草園家屬自助團體合作,成立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首重由家人陪伴家人,照顧者傾聽照顧者,讓家屬們透過課程、支持團體去陪伴彼此,家屬團體的核心成員因著感同身受,也時是比專業人員更即時的不需評估地進到家裡、醫院去陪伴其他家屬,形成家連家的結盟與凝聚力量;另一方面照顧者專線的功能在於,將家屬的經驗知識提取出來,進而釐清家裡發生的故事與專業/社會支持體系之間現行的距離、家屬是如何在其中摸索前進,以及箇中辛苦。現階段人力的不足致使我們仍然只能先在專線上、聚會地點中守候,可是還有許多家門出不來的精障者及家屬,該怎麼辦呢?
這當中有「量」的問題,有「質(團隊)」的問題,有「系統」間的問題。先要提高社區訪視的人力,品質才可能提昇,才可能做到建立和精障者的關係,從而長期支持(這個疾病需要長期、慢性控制);然而品質也不單是量的提昇,因為是跟一整個家庭工作,家庭成員之間也充斥著差異,所以單是以一名工作者要進到家庭系統跟家庭工作,是非常艱難的。另外家庭的需要往往也是多元的,資源連結有其盲點,有時一個服務對象卻有多達近十個單位服務,這可以討論個案管理的改進,可是工作者最大的盲點不是個案管理,而是視框總是不夠廣,一個人所能發揮的服務想像力不足,家庭所面對的現實也涉及到許多面向,因此應該發展團隊有多元觀點進入家庭的工作方式(可參考國外的精神治療:開放式對話)。這樣的家庭支持計劃,就可以連接到住院需要、出院準備、到宅服務及社區發展支持計劃。
以上所說,一定有不夠完備處,持續思考、行動,這需要大家一起建構,而不只是究責、指責而已。前述分享,僅以挑起一磚一瓦的社會工人自期和跟我一起造橋舖路的夥伴們。
公庫按: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 <服務對象> 精神疾病經驗者的家人或朋友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13:30–20:30 <電話專線>02-2230-8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