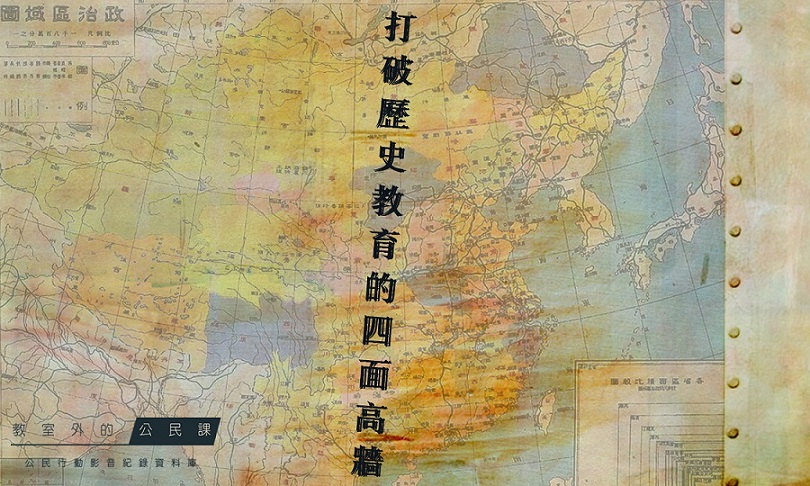文/ 許全義(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
「等待,唯有死亡;祈求和平,唯有被侮辱;低聲下氣懇求諒解,唯有被譏笑;盼望正義援助,唯有被誤解我們甘願被奴隸。……我們並不是缺乏勇氣,我們並不是貪生怕死,我們現正遵從你們歌頌的方法,追求我們台灣的完整獨立,追求我們台灣民眾的自由與幸福,……,我們並不準備讓你們歌頌,但求苦難的同胞,不再被壓迫與奴隸,求世人對我們苦難的同胞,賜給他們獨立、自由與幸福,我們深信壓迫與奴隸存在時,自由與幸福等於奢談。唯有壓迫與奴隸消失時,自由與幸福得以保障,人權得以伸張,世界能夠和平。」 無法送達的遺書
爬牆,如少女時代所描述的,好像是台灣高中教育的共通記憶,甚至是身分認同,如台中一中學生在學校高壓取締爬牆時,喊出,”不爬牆,還是一中嗎?”
高牆似乎一直是威權或不合理政治體制的象徵。如印度在不列顛帝國殖民時期,甘地也爬牆。他穿過印度從北到南的,防制私鹽販賣的綠牆,步行到海邊,舀盆海水,靜候太陽曬乾,嚐一下海鹽,然後就被帝國警察帶走。甘地透過爬牆,凸顯帝國為了經濟利益,鹽巴公賣,妨礙民生之不合理。
打破隱形的牆,更是歷史發展的隱喻。如孔子打破他那個時代,貴族、平民之間的高牆森嚴,開辦講學,學不厭,教不倦,普及教育。伽利略也是爬牆高手。他那個時代的物理分為:天域物理,月亮以上係由乙太組成的水晶天,不會生成變化。地域物理,月亮以下屬地水火風組成的,會生成變化。伽利略打破此高牆區分,說月亮上面也是坑坑洞洞,太陽也有黑子,天域、地域都適用同一物理法則。換言之,徵之史實,大師之為大師,就是打破高牆,某種有形無形的、武斷的分類體制。
本文以下,將以高牆作為威權時代遺蛻,檢視台灣歷史教育亟需轉型正義照亮的陰影:一、知行區隔。二、分科穀倉。三、大中國主義。四、政治中心。
一、 知行區隔
人是歷史動物 ,會透過過去的經驗學習。如動物一般都怕火的,人本來也是。後來,透過經驗累積,才學會克服對火的恐懼,學會用火熟食,演化躍進。又如1960年代,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彼此對峙,有核子冬天的危機。今天,我們已經很難想像,美蘇兩國會發動核子戰。又如我們知道臭氧層破洞,是因為冷煤使用氟氯化物之後,全球協作之後,不再使用氟氯化物當冷煤,也就減緩了臭氧層破洞的問題。
這種認識過去,釐清問題,邁向更美好未來的態度,是為歷史意識。
台灣有歷史意識嗎? 如果把知行分隔開來,說歷史意識只是認識到過去與現在迥異,這個問題當然超級白癡。台灣人,毫無疑問,大家都有。
不過,我們如果以左派的眼光來看,這問題就很不確定了。就馬克斯來講,意識是要喚醒。工人階級意識不會因為自然受到慘無人道的壓迫,就自然形成。這種意識需要不斷的溝通,命名,對話與行動來打造。當階級意識沒被喚醒時,還是會有很多明明受壓迫的工人,反過來壓迫工人。同理,當性別意是沒被喚醒時,女人同樣會陷入為難女人的歷史窠臼中。
換言之,歷史意識不只是一種思維,也不只是個人之事。她需要串聯眾人,反思,共同命名,對話,說服與行動的澆灌。
就此看來,反思與命名是台灣歷史意識的起點。語言清晰是當務之急,如有人認為種族淨化一詞,刻意隱藏”婦女、兒童與老人的大量屠殺,對於婦女及女童(有些甚至只有五歲)的強暴”。這些罪行在”淨化”的字眼下,彷彿就有了正面的意義,我們好像可以去追求現實的『淨化』,而將種族的”污穢”歸於受壓迫者。
台灣是中華民國嗎? 這樣講,語言清晰嗎?大家可以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民無法代表中華民國國民全體,所以不能享有主權嗎? ( 憲法第二條 )所以台灣人民不是國家主權所係,政府可以不接受民意指揮與監督。如核四公投提案,只有十三個人的公投審議委員,就可以否決十二萬人公投連署民意。馬英九一個人的意志,就可擋下上百所高中生的義憤,一意孤行推動程序不正義,外行指導內行的微調課綱。
如果中華民國的版圖是秋海棠,而台灣只是其中的邊陲彈丸之地。那麼曹永和先生所提倡的多元文化下的台灣島史就無由成立。台灣史,就只是會像連橫所寫的台灣通志一般,台灣價值體系就存在於生出多少貞節列女,有多少人考上科舉,接受了多少儒家文化等等。
我們走在台中街道上,象徵儒家文化的明德路,篤行路,代表中國各地的北平路、西藏路等等,語言清晰嗎? 這樣的命名可以反映台中城市街道的歷史生命嗎?二二八事件,這種命名清晰嗎? 武器極度不均衡,人民又無造反之意,又不分青紅皂白,不容抗辯,為什麼這樣不叫”屠殺”呢?
如果這些都不明不白,也就意味的台灣連適當命名都還沒啟動? 那怎麼可能已經喚醒其歷史意識呢? 一個沒有歷史意識的人,就像孤魂野鬼般,沉溺在永遠的零中,過去、現在、未來糊里糊塗,當然不ˇ可有行動力,塑造未來,雕塑自己的命運。
如此,台灣人就陷入莫名其妙的悲觀與虛無當中。韓片華麗假期,描述的是國家機器屠殺青年學子的悲慘世界,但我相信,看過此片的人都會感受到韓國人民追求人權,公平正義,無與倫比的樂觀鬥志。圖博片高山上的世界盃,描述的是圖柏遭中共血洗、資本主義全球化侵略之後,所造成的文化傳承不易,花果飄靈的窘迫處境。可是看過的人,或多或少會感受到圖博人彼此同情共感的溫馨與樂觀態度。可是我們看台灣講二二ˊ八的”悲情城市”,講白色恐怖的”少年牯嶺街殺人事件”,就是一路陰沉悲觀到底。
台灣的悲觀虛無,幾乎無所不在。如環境史的紀錄片,黑、看見台灣,問題紀錄深刻詳實,也把台灣高空鳥瞰場景拍得很漂亮。可是,面對山河破碎,汙染處處,這些紀錄片何嘗呈現出台灣人民做為行動者可以扭轉此趨勢呢? 它們給我們的印象,還是一路惡化下去的悲觀氛圍。相對的,中國的塵霾空屋問題遠比台灣嚴重,可是柴靜的紀錄片,反覆闡述的還是樂觀的,中國人終究可以解決此問題的,就像過去英國人解決倫敦空汙問題、加州天空會回歸藍天白雲一般。我們就更不用跟素以樂觀態度文明的美國環境問題的紀錄片了( 如不願面對的真相 )。
我們台灣為什麼會那麼悲觀? 為什麼會覺得自己甚至當個雕塑自己命運的行動者,都不可能?
台灣有歷史意識嗎? 我們真能串聯眾人,反思,站在過去的基礎上,共同命名,對話,說服與行動,來塑造我們的未來嗎? 答案就在我們每個人的抉擇上。
總之,或許因為台灣一直居於帝國邊陲,或受殖民統治,知行區隔、斷裂,陷於歷史虛無主義。我們追求教育轉型正義,當致力於打破知行區隔的高牆。
二、 分科穀倉
知識就是力量。史學是認識過去,解決問題,超越既有限制,邁向更美好未來的學問。
問題就是問題。它並不會因為被塞進分類架構中,就獲得簡化,單純成為歷史問題、地理問題或公民問題等等。它甚至還要超越自然與人文,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鴻溝或高牆,才能獲得釐清,如《利維坦與空氣幫浦》一書中,所描述的英國十七世紀的體制危機。
此故,美國高中SAT,歷史就涵蓋了台灣整個高中社會科,尤其是有著相當深入的”公民”議題,如討論哥倫布用兩本航海日誌,一本自己看,講的是船航行實際路線;另一本給其他船員看,就抄過去去印度的航海日誌。他們就會問,做事情可否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又如討論馬丁路德,黑人人權史, I have a dream的演說時,幾乎毫無例外的都會討論學生各自對未來的夢想。北歐國家甚至連美國歷史和自然科學兩大範疇放棄了,改成問題為中心,解放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的力量。
中學教育應是一般公民彼此分享討論的溝通基礎,而不是像專家一樣,在高度分工下,探索人類未知的領域。我自己在台中一中社會科辦公室中,歷史老師一區,地理老師一群,公民老師一圄,彼此分隔,互不通聲氣。更不用說,自然科與社會科協同教學了。
在這種情況下,學生雖然讀了很多有的沒有的知識,可是要一起討論土石流、地震、災難、食品安全、空汙問題等等,卻顯得困難重重。這種溝通困難在浩鼎案中,就可見一斑。學法律的和生命科技從業人員彼此之間,恍如雞同鴨講。如辦案人員看到浩鼎案,腦袋只想著「他們事先知道可能會失敗,因此出脫股票」。可是,知道醫學臨床試驗的人看到的是:原來浩鼎使用不同的藥物效力評估指標,因為藥物要產生「無惡化存活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可能先惡化後來好轉卻被判定為無效),而且其它研究告訴我們「需要時間才能產生抗體反應」,如果試驗時間不夠長,就可能會被視為失敗。究竟要多長,也不易判斷。所以,難道不應該先試驗「無惡化存活期」,再進一步試驗「整體存活率」嗎?檢調單位又如何能知道浩鼎不會在後續的試驗中使用「整體存活率」的評估指標?他們如何能判斷浩鼎不是在追求此項技術和檢驗上的嚴謹性呢?
我們今天專求轉型正義,塑造更合理的公民社會,要促進公民討論,在高中階段,不宜太早分科,反而要打破分科穀倉,很多公共事務,才能好好討論,說清楚,講明白。
三、 大中國主義
台灣歷史教科書,除了世界史之外,可以說只是漢人史,有著濃濃的大中國主義。
這種大中國風,讓美國人都覺得很遺惑,因為台灣竟然和16個國家有領土糾紛,包括宣稱整個中國都是我們的。台灣的宣稱領土裡,和「我國」有領土糾紛的國家,計有:中國、蒙古、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孟加拉、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日本、北韓「最荒謬的是,如果他們宣告放棄了這些領土,會被視為一個台獨的挑釁。」
而引起眾怒的黑箱課綱,正是將台灣擋在大中國圍牆內的產物。那份課綱羞與台灣公民的過去站在一起,反而希望在大中國口號宣傳中遺忘台灣公民的共同記憶。這份課綱所宣揚的其實是台灣人所不可能享有的中國幻想而已。一如以中國古典形式所建構的南海學園、忠烈祠、圓山飯店和中正紀念堂一般,那只是幻想擁有整個中國的、不切實際的規劃。台灣不是中國歷代中的南朝,各城市也絕非北平、天津、西藏路星羅棋布的小中國。新時代台灣公民要對自己的共同記憶尊重。羞與台灣公民站在一起,不斷陷入新政權擁有者否定前一個的過去之井中的課綱,終將在歷史洪爐中化為灰燼。
大中國主義的粗暴分類體制,會投射到台灣課本對中國上古史的理解。就算在中國史課本總壟罩在大一統史觀下,時代錯亂,犯了用現代眼光來看過去的謬誤。如陳豐祥先生所寫的中國史,高中歷史二的第一章第一節。
史學從十九世紀發展以來,最基本要求是不能時代錯亂,或用現代眼光看過去。一定要注意史料的年代限制,如史記成書於漢代,會將漢代大一統格局,投射到它所描寫的”夏商周”三代。同樣的,戰國策成書於西漢末年劉向,也會有此限制。
大一統格局下,書同文,車同軌,還有複雜的行政體制,所以還可能有足夠的統制技術,處理幅員廣大的王國。可是如果連文字都還不成熟,那麼該王國的實質影響力就相當有限了。
準此,假設夏成立的話,在文字未成熟的情況下,其版圖幅員勢必相當有限。學界一般也相信,夏商周三代真能統御的版圖,很難超過今天日本的大小。可是,我們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作者,陳先生卻用禹貢九州圖( 頁十四),相當於今天中國的版圖,來描述夏代;把整個海岱地區、中原地區、江浙地區和兩湖地區都當成是商代的國土疆界( 頁十八)。 這不是明顯違背學術倫理嗎? 教學生時代錯亂的”歷史知識”嗎?
陳教授在課綱限制下,把二里頭文化直接當成夏文化的發掘,還情有可原; 可是,順著課綱,罔顧學術倫理,用大一統史觀來解釋整個夏商周,就真是太過分了。
又有關人類起源的問題,目前隨著考古出土資料愈來愈多,還有DNA檢定溯源,人類祖先源自東非,日本祖先來自台灣,華北中原地區開始有智人入住不超過一萬年,殆無疑義。我想,陳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結果他寫高中課本,卻還是硬扯”中國本土應是早期人類文明的搖籃之一”( 頁六 ),將人類單一起源理論模糊掉,又跟多元源起混在一起。
他這麼做,除了要滿足中國民族主義的浮誇想像之外,實在很難同情理解。
不過還有令人百惑不解,有關中國新石器時代文明,一般都會說到很多文化地域,如巴蜀地區、兩湖地區、江浙地區、甘青地區、中原地區、海岱地區( 山東半島 )、雁北地區和燕遼地區。並藉此說明,為什麼中原地區,位於各區大小相當,又有某種程度差異的文化交匯地會興起。為什麼中國會稱為”中”國。
可是,陳先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分布圖卻只有中原地區和海岱地區。其他的都不見了。課本正文敘述甚至連名聞遐邇,不下於殷墟的三星堆文化,也完全沒提到。好像從古至今,”中國”就是中原地區和海岱地區掌握政治文化優勢一般。
陳先生所依循不只是大一統中國史觀,或許還窄化到大一統北京史觀去了。並且在此狹隘的史觀主導下,無視考古學界中可說是定論的研究成果了。
大一統歷史觀的粗暴分類體制下,也讓我們看不到中國各地的特殊性。如”四川畫像呈現不同的世界,大量的畫像描繪日常生活的種種,他們對於古賢烈士、忠臣孝子和男女大防的想法並不重視。或許也可以說成都平原的男女之防與道德界線,比起儒家思想濃厚的山東來說,較為的開放。天府之國,不僅吃穿不愁、生活愜意,且情慾之事也較其他地方開放。看到這兩塊畫像磚,有點讓我想起小時候在台灣鄉下,有時葬禮或是酬神的活動中會請電子花車來跳脫衣舞,讓往生者和神感受到人間世界的喜悅和歡愉。”
如此我們所讀的中國史,往往只是帝王家譜,或勝利者的故事,無法對稱性的,同時處理:殖民者、被殖民者;壓迫者、被壓迫者;成功、失敗的;中心的、邊緣的;典範的、異例的……..等等。可以對稱性處理史事,是史學的特有優勢。因為不管我們所研究的成功、失敗,聖賢愚昧,跟我們迥異或雷同……都已化為春泥,我們都可以不計較,也都可以文本資料之上,拼湊出另一種聲音。
如三國志中記載:
鄭渾……復遷下蔡令,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
文本表面的意思是,漢末天下大亂,下蔡、邵陵的人民,紛紛拋棄農耕生活,轉為漁獵。他們生了小孩也無法養活,所以大都棄養。鄭渾到任後,奪了老百姓的漁獵之具,開稻田,勸民務農,並以重法禁絕殺嬰之俗。
當我們對稱性理解,想到民眾的經驗時,就可能有不同的圖像出來。鄭渾真的是好官嗎? 好官會限制人民職業自由,只准民眾從事農耕嗎? 會侵奪普通人民的生產工具嗎? ( 漁獵之具 )會讓日子都過不下去的人民,重加以刑罰,逼他們生養小孩,讓日子更悲慘嗎? 農耕文化會真的比漁獵文化更好嗎? 如果是,那又是誰的? 國家的? 還是人民的? 文化上的? 還是環境倫理的? 小孩子的? 還是大人的?
只有當我們打破大中國主義高牆,讀歷史才不會那麼輕易掉入,歷史是勝利者的紀錄的窠臼,或用現在眼光來看過去的輝格史風之中。如有關鄭成功的評述,史學名家汪榮祖和傅衣凌都因為侷限在大中國高牆下,犯了過用現在眼光看過去的毛病。
鄭氏將台灣自荷蘭手中奪回,成為中國人的土地;而施琅攻克台灣,清朝置為郡縣,始與大陸統一。………故就台灣內屬而言,施氏功勞猶高於鄭氏。但在歷史上,鄭氏被褒為民族英雄,流芳百世;而施氏被貶為叛將貳臣,遺臭萬年。這種道德裁判多少帶有舊時代的標準,所謂忠奸之分大都以一家一姓為對象;只講道德的對錯,而忽略事理的是非。
汪榮祖,施琅與台灣
資料二
鄭成功與施琅雖然處於敵對的位置,他們征台的動機也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則有同樣的認識,都堅定地主張保衛台灣。從他們兩人對於台灣的認識來說,我們說:施琅不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
傅衣凌,施琅評傳序
這兩段資料都預設台灣遲早會跟中國統一,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他們認為要為施琅平反,彰顯他使得台灣劃入中國版圖的功勞。不過在當時,台灣是否內屬中國無關宏旨。清朝皇帝康熙本身就想把台灣丟掉。而在此之前,台灣與中國交流,從考古資料來看,也超過一千年以上。其間,中國從不覺得將台灣納入版圖是件重要的事情。
用台灣歸入中國版圖這個標準來評價、解釋鄭成功與施琅之間的關係,也就犯了用現代人眼光來看過去的問題。在史學方法論上,這還有個專門術語,輝格史風( whigish ),來說明這種歷史解釋。輝格歷史解釋會將過去簡化,濃縮到現代來。那麼過去的歷史就喪失其獨立性,只是現在的附庸,無法豐富我們的參照觀念架構,反思現在的限制。那是很可惜的!
四、 政治中心
教育是百年大計,不是政治的工具。很遺憾的,或許台灣繼受中國以吏為師的傳統,在教育現場上還四處都是威權政治遺蛻,如國旗(國民黨黨旗),國歌(國民黨黨歌),國父(國民黨總理),蔣公(國民黨總裁)。我以前讀高中時,全校老師也只有兩個人不是國民黨籍。
這種威權政治中心的高牆,讓台灣歷史教育嚴重落伍,幾乎還停留在百年前。如中興黑森林社所說的,教育轉型正義,刻不容緩:
“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全球掀起民主化浪潮,各國致力於轉型正義以檢討舊政權的不公義,撫慰被害者之傷害為一重要面向。因此,轉型正義其中一個目的即是停止歌頌壓迫人權的獨裁者,避免對受害者及其後代造成二度傷害,除此之外,更有教育人民反思威權體制的不公義,促進基本人權價值的認識之功能。
尤其台灣社會自蔣政權時代以來,國家機器利用黨國優勢將蔣介石銅像林立於中興大學等高教空間,淺移默化其權威性、灌輸崇拜獨裁領袖的思維,長久干預人民之思想、言論自由。因此解嚴之後,為實踐民主價值、保障人權,本應先拆除銅像,還給人民免於恐懼、傷痛的權利,然而政府似乎未意識到其重要性,在全球轉型正義機制逐漸完善的對比之下,顯得突兀而令人遺憾。”
銅像拆除便是一場直接的民主教育示範
本社需於此重申,拆除銅像絕非激烈、毫無判斷之手段,而僅是將人民本有之權利交還,使威權的符號及其象徵意義不再以幽微的方式干涉學生乃至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而得以為轉型正義開啟初步之對話。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時間的推進、人權教育的落實、公權力的行政透明亦為不可或缺的要素,台灣民主化開花的結果一直是得來不易,而歷史是人的作為,我們即是現在歷史的一部份,直接打破威權是一重要的民主示範,刻不容緩。”
此政治威權中心,反而讓台灣歷史教育在面對宗教與人權問題上,嚴重失焦。如以孫若怡編的選修歷史下為例。
當上帝已死,宗教與斂財難分時:如台灣還有鼓勵放生的宗教,導致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也可找到幾乎如手臂一般粗的眼鏡蛇,顯然是進口來 。信仰淪為戰爭溫床, 如以阿戰爭,印度與巴基斯坦用原子彈互瞄 時,在中學要學甚麼樣的宗教史,才不會失焦,才是有意義的?
這問題在101課綱中,似乎不曾好好思考過? 導致在孫博士所寫的課本引導下高中生,要記誦吠陀信仰的重要神祇( 頁9 ),知道婆羅門教的三大主神 ( 頁10 ),熟悉神猴哈奴曼的傳奇( 頁20 )。我真是不知道灌輸學生這些內容,到底在他討論宗教與社會時,有什麼意義可言?
教科書不是旅遊雜誌或百科全書,不是要學生知道一些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的瑣碎內容,而是提供學生結構性肌理,認識自身所處的當代社會。在有限課程時數下,孫博士要學生討論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教義與發展的異同之處( 第一章問題與討論第一題),究竟要訓練學生甚麼能力,呈現甚麼重要性?
衡情而論,我們歷史課本的”宗教”,一直在教派、教義和經典內容上盤旋,恐怕失焦了,而且有灌輸某特定宗教意識型態之嫌。如他說,”任何一個人,只要肯臣服於真主的意志,敬拜真主,並深信祂的懲罰與獎賞,他就是ㄧ位”穆斯林”。” “七世紀,先知穆罕默德開始宣揚真主的信條”( 頁 41 )。這些都不是比較宗教學的口吻,更不像台灣歷史教科書,反而像是伊斯蘭教的教義問答。
理論上教科書在理論縱貫程度,協助學生理解當代社會的宗教問題上,要高於電影這種通俗文化,可是我們如果比較”來自星星的傻瓜(PK)”和康熹版選修歷史下,就會發現我們的歷史課本寫宗教真是寫得一蹋糊塗。
PK主要透過一個外星人的眼光,來看印度的宗教問題。其概念大致上就是人類從外太空拍回地球圖像後,看不到人為畛域所引起的反思。
PK將不同教派的人,服裝調換,結果號稱可以感受上帝或神意旨的印度教教主就惑於表象,如把穆斯林視為基督徒,把印度教徒視為穆斯林。大家都是人,每個教派都將人視為神或上帝的子民,都強調慈愛,雖然各教派儀式、服裝、經典不同。有的要穿鞋進去,有的不可。有的供奉椰子水,有的用紅酒,有的不可喝酒。…….這些不同,一如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有的閃亮亮,有的烏漆,有的緊,有的鬆……但脫光後,就跟天上飛的鳥和PK星球上的人光溜溜,沒甚麼兩樣。
然而,這些差異,卻被宗教體制擴大,成為無法跨越的鴻溝。如印度教教友和穆斯林不能通婚,雖然彼此情投意和。
為什麼本來都強調愛與慈善的宗教,變得如此冷血與殘忍? pk認為是神跟人之間的中介出問題了,WRONG NUMBER,好像撥錯電話就無法溝通一般,神職人員也無法傳達神的旨意。神寧可省下浪費澆淋在碩大神像身上的牛奶,救濟窮人。神不可能反對穆斯林小女生上學的求知欲。神與其透過神職人員,變出金項鍊,或騰空飛起展現奇蹟,還不如解決人間世的貧窮問題。
可是ㄧ般人為什麼還是會信那些無法跟神溝通,撥錯號碼的神職人員或偶像呢? 一言以蔽之,神職人員販賣恐懼。pK 在考場前,弄顆石頭,塗紅,擺設簡單的祭壇與奉獻的錢,沒多久就吸引一大堆人來祭拜。他們排隊奉獻金銀,匍匐乞求,惟恐自己無法考上大學。
pk 似乎無厘頭,卻成功挑戰宗教,返回天鄉時,其實也在展現甚麼是啟蒙:破除中介,勇敢活出赤裸裸而健壯的自己。
簡之,這部談論宗教問題的寶來塢娛樂芭樂片,無論觀眾同意其見解與否,很有層次的說明了:人為什麼需要有宗教? 為什麼現代社會會有各式各樣的宗教差異? 神職人員中介宗教所衍生的問題? 並訴求破除中介與表象,並透過愛來化解宗教衝突與紛歧。
反觀我們高中歷史課本在談論宗教時的結構肌理何在? 焦點何在? 有甚麼問題性? 要解決甚麼問題?要學生背誦那些有的沒的宗教流派與教義的用意何在? 難道只是灌輸政治意識形態,讓學生考試有個依據,在大學聯考時拼輸贏嗎?如果只為考試而編課綱,寫書,像孫先生編的書,卻沒有甚麼知識素質,沒有引導我們前進的力量的話,那真是失焦了。
當一個編寫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教授在宗教議題上的反思,還比不上印度寶來塢電影時,台灣社會一天到晚發生wrong number 或宗教神棍,騙財騙色的案例,也就不足為奇。歷史課堂不應該是政治的課堂,而是社會的,讓學生處於現代社會,對於生命、宗教、環保、人權、經貿、族群、階級和性別等諸多問題,有充分的思考與討論。政治只是一時的,不應該成為歷史教育中唯我獨尊的高牆。
總之,台灣教育轉型正義,刻不容緩。如何打破這四面高牆,知行區隔、分科穀倉、大中國主義和政治中心,讓教育不再是政治的奴僕,回歸百年樹人的社會脈絡,還有待我們好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