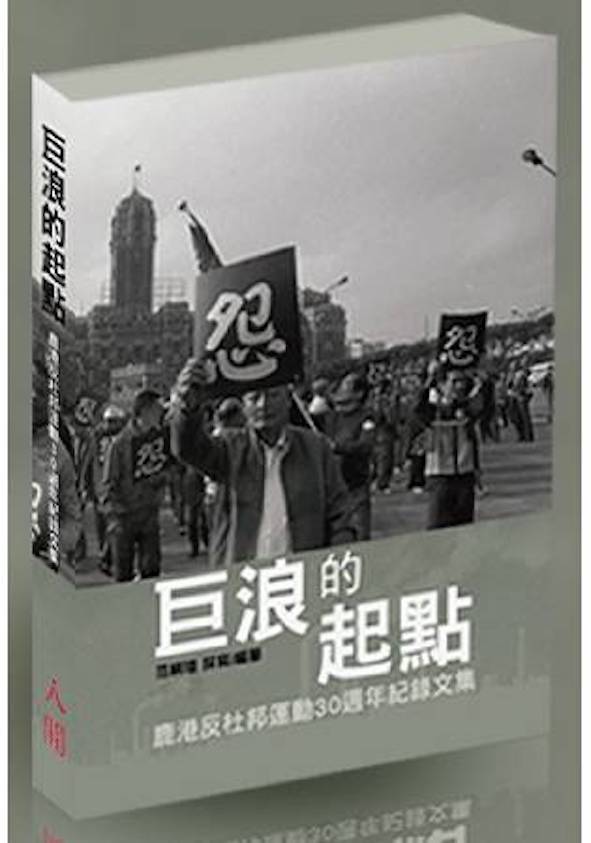文 / 陳信行
多年之後,二氧化鈦(鈦白粉)終於從被認為「絕對安全」,轉而在2010年被被國際癌症研究組織(IARC)列為2B類,可能的人類致癌物。
多年之後,當初執意要在鹿港旁邊蓋超大型二氧化鈦廠的美國杜邦化學公司,由於開始輸掉它的另一個重大產品──鐵氟龍──的環保訴訟,眼看可能必須賠償大量罹癌勞工與居民,而在2015年初先改名分割、後與道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s)合併,並計畫把合併的公司再拆成三份,讓「杜邦」這個風光兩百餘年的金字招牌,在法律上神奇地消失無蹤,從而使得受害者求償無門。
被鹿港人趕走,最後落腳在桃園觀音的杜邦二氧化鈦廠,究竟有沒有嚴重污染環境,還沒有人清楚。但是,杜邦在美國密西西比州海濱的同型工廠,已經有數千居民與勞工提出求償訴訟,至今未決。杜邦2004年提案要設在中國大陸山東東營市黃河三角洲海濱的同型工廠,環境風險受到高度的質疑,至今建廠工程還沒下落。
至於鹿港人,雖然沒有在1986年趕走杜邦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但是,至少需要擔心的事少了二氧化鈦廠這一件。而且,在一場更盛大持久、更受到社會各界廣泛支持的抗爭之後,彰化居民在2011年又趕走了國光石化設廠計畫,避免走上雲林麥寮的厄運。環境運動,已經是台灣社會最成熟的民間力量之一,而這段歷史必不可免地會從鹿港反杜邦說起。
但是,在1986年1月5日,當鹿港居民第一次舉辦反杜邦座談會的那天,恐怕只有具有最狂野的想像力的人,才會預料到今天這種發展。
在那一年,統治台灣的還是一個數十年來處於軍事戒嚴狀態的反共親美右派獨裁政權,異議者理論上都可以輕易受到最嚴厲的國家暴力鎮壓。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霸主、杜邦化工是世界最大最老最先進的跨國企業之一。按理說,美國杜邦化工要到台灣的哪個窮鄉僻壤投資設廠,「老百姓」只准夾道歡迎,各級政治人物除了表忠獻媚以便順道撈點油水之外,不可能另有意見。
掌握政權的人,除了決定誰貧誰富誰活誰死之外,還壟斷了真理,以及所有的善惡美醜的定義權。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凡是附和這種森嚴等級的,都會被官方媒體與學界稱做「客觀、理性、公正」,反之,則是「主觀、情緒性、偏激」。而這些,從鹿港反杜邦那時開始,都將開始改變。
但是在1986年初的鹿港,反杜邦的群眾與運動幹部應該都還料想不到,非但他們的抗爭會在幾個月後勝利、戒嚴會在翌年七月解除,而且,號稱最老牌、科技最先進的美國杜邦化學公司,有可能會在他們有生之年衰亡。
杜邦、美國與台灣
註冊在美國東岸德拉瓦州的杜邦化學公司(E. 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原本是在19世紀初由一位逃避法國大革命的流亡法國商人成立的火藥製造廠。從創始時期供應火藥給美國軍方開始,杜邦一直是「軍事工業複合體」的成員之一,在20世紀中期也承包了原子彈和氫彈研發的部分工程。杜邦也開發了包括人造纖維尼龍、冷媒氟氯昂(Freon)、不沾鍋上的鐵氟龍、以及各種農藥和電子工業用化學品在內的一系列重要化工產品。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煤礦、蒸氣機、機械紡織機、火車、輪船打造的科技體系可說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把成千上萬的農民改造成雇傭勞動工人。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工業中,絕大多數是雇用數百人的,現在看來屬於中型的企業,隨著景氣起起落落。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社會面貌就很不一樣,以化工、電氣、石油、鋼鐵、汽車為核心的這一波新型態工業,多半是壟斷企業打造的龐大的科技體系,雇用專業的科學研發人員開發新產品,以專利權保護產品的壟斷權利。
杜邦化工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第二波工業革命」企業,掌握許多重要專利、在世界市場上一些產業部門長期握有可觀的市場占有率。杜邦家族同時還長期通過大量控股掌握通用汽車(GM)、康菲石油(Conoco)等關鍵財團的經營權。艾森豪任命通用汽車總裁威爾遜(Charlie Wilson)為商務部長時,威爾遜說了句名言:「凡是對通用汽車好的,就是對美國好。」這時候通用汽車的董事長就是杜邦化工家族第五代的掌門人皮耶.杜邦。這家公司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可見一端。皮耶.杜邦也長期擔任麻省理工學院(MIT)董事,是重要捐款人之一。可想而知,在美國冷戰勢力範圍的邊陲,杜邦這種影響力遍佈美國政、學、軍、商界的大企業,對台灣政府官員而言,簡直就是難以觸摸的崇高權威。
當年在台灣政府裡支持杜邦在彰濱工業區設二氧化鈦廠最重要的群體,是一群後來常被商管媒體譽為「台灣經濟成長的推手」的「技術官僚」:李國鼎、孫運璿等等。連同嚴家淦、尹仲容等人,這些幾乎一概是理工學科出身、有些留學英美經驗的官員,從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就被認為是充斥著軍頭、特務、黨官僚的黨國體制內,比較現代化的一群。1950年代台灣政府大量倚靠美援時,這些相信現代科技與自由市場的新派官員受到美國政府信任,主導著財政、經濟、交通等部門,以及美援會等左右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機構。從全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的設立,到後來設立科學園區推動半導體與電腦產業,這群工程師出身的經濟官員,都是重要的推手。他們對「現代化」這回事,及其相關的一切事物,幾乎都全心全意地信仰。例如,嚴家淦就常說「數字是不會騙人的」。事後看來,這種對於「現代化」近乎於宗教的信仰,在20世紀中葉,其實是各國政府官員以及學界主流的常態,不管是在哪個陣營、哪種政經狀況的國家。
理性計算的工程師式「現代化」官員,和惡狠狠的軍警特務,看來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但是,在1986年的台灣,這兩者其實是相互合作無間的。現代化工業經濟成長與人民的生活改善,合理化了威權統治;而任何對於政府領導的發展道路質疑的聲音,黨政軍警特等國家暴力機構都會負責消音。這在鹿港反杜邦的過程中,許多人會親身經歷到。
同一個時代經歷過美國扶持下的政治威權統治與經濟高度成長的,還包括南韓、智利、印尼、泰國等等;但是政治上右派威權統治、經濟成長卻並不高的國家更多。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美國影響下的國家,經濟成長的同時,舊社會的貧富貴賤之分或是新出現的階級分化,多半會更嚴重。1965─1980年的台灣是個異數,家戶收入不平等不升反降。因此,在1980年,台灣經濟官員郭婉容在其著作中驕傲地稱台灣為「兼具平等的成長」。雖然在此豪語發表之後的三十幾年,台灣的所得不平等持續、加速上升。但是,在那一年,台灣顯然成了模範生,其經濟政策成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資本主義國際機構大力推銷的成功之道。
到底什麼是戰後經濟發展的台灣道路?各領域研究者可以不斷辯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對杜邦這種美國大企業的投資熱烈歡迎、高度優惠、低度管制,是一個必要成分。後來被揭發,在營運的二十幾年間嚴重蓄意污染地下水,並導致數千員工罹癌的桃園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就是這樣的例子。在孫運璿主導下的「RCA計畫」受訓的許多技術人員,後來都成了台灣高科技業的新貴富豪。但是,他們走向成功之路的代價,是另外一群基層勞動者的死難、和難以恢復的環境破壞。
要不是1986年的反杜邦抗爭,原本,類似RCA集體癌症案這樣的事,很可能現在就已經在彰化爆發了。
如果當年鹿港沒有反杜邦
杜邦在向台灣提出在彰化設廠的提案之前五年,於美國密西西比州海濱的貧窮漁村德立爾(DeLisle)設立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二氧化鈦廠,首創將高濃度廢液灌注到2、3千米深層地下水層的「環保」技術。由於當地長期的貧窮,居民非常歡迎有工作機會來到當地。但是,十餘年後,各種怪病就開始發生,尤其是在大量食用當地海灣的海產的漁民家戶中。
二氧化鈦是從油漆色料到食品添加物都會使用到的常用化學品之一。從礦石提煉出來,有兩種常用技術:硫酸法和氯化法。硫酸法是最常見的,因為處理低品級礦石比較有效。但是硫酸法會產生大量強酸廢水和其他有毒廢棄物,以往的工廠往往社在海邊、用弱鹼性的海水來沖淡廢水,造成嚴重污染,歐盟因而從1978年起(當時還只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特別立法規範各國的二氧化鈦廠的環保標準。氯化法是杜邦的專利,理論上可以通過廢水再循環降低排放廢棄物的量,但是需要使用高品級的礦石。使用低品級礦石時,氯化法的環境污染嚴重程度和硫酸法差別不大。而且,兩者都會產生具放射性的鈦礦廢渣。
杜邦打算來鹿港設廠的1985年,有5個二氧化鈦廠,其中只有密西西比的德立爾廠和墨西哥廠使用低品級礦石,另外三個設在美國的工廠使用它的氯化法適合的高品級礦石。這5個廠每年總產量高達50萬公噸,約佔世界總產量的20%、美國市場總產量的一半。1986年5月到6月,杜邦公司招待台灣考察團[1]去美國所參觀的德拉瓦州廠,使用的是排放污染物確實比較少的高品級礦石氯化法。但是在鹿港的設廠計畫,是使用低品級礦石。因此,最後發生在密西西比州海濱的狀況,是當年如果杜邦順利設廠後,最可能會發生的情形。
密西西比州是美國各州中環保法令最寬鬆、執法最無力的州之一。長期的貧窮和政治改革緩慢是原因之一。1950年代末黑人民權運動興起時,密西西比也是州與地方政府最抗拒改革的地方。1980年代雷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密西西比州把大量環保稽查工作讓給「廠商自律」。而根據杜邦公司自己的監測資料,德立爾廠的環保措施是「最先進」的,毫無問題。州政府方面,由於實際稽查工作的稀缺,並沒有太多關於杜邦德立爾廠的排放水、空氣、廢棄物等的具體資料。大多數時候,州政府稽查員只是檢查杜邦公司的書面紀錄是否完善。但是,根據美國聯邦環保署在1984年印度波帕事件的衝擊下所建立的全國有害化學物質排出目録(toxic release inventory),杜邦德立爾廠是全國排放戴奧辛的量第二高的工廠,第一高的是杜邦總部所在的德拉瓦州的另一個廠。
從1990年代起,德立爾附近的居民以及廠內員工發現身邊罹患嚴重怪病的人出奇地多,因而從請願、要求聯邦政府調查、一直到後來有近2000人對杜邦提起侵權訴訟,但是杜邦的律師有效地使得訴訟拖延多年無法開庭審理。原本受害者想要提出集體訴訟(class action),法院最後也沒有裁准,他們只好一案一案地告下去。原告甚至雇用了科學家檢驗了幾百位居民血液中的戴奧辛含量,以做為證據。2005年,終於有第一位受害者斯特朗(Glen Strong) 被密西西比州地方法院陪審團判決:杜邦的污染行為與他罹患的多發性骨髓瘤(一種血癌)有因果關係,杜邦必須賠償他1550萬美元。
斯特朗先生是蚵農,家族沒有血癌病史,他認為他的血癌是由於長年食用含戴奧辛的牡蠣、以及在居家環境的空氣、土壤、飲水中暴露到超標的戴奧辛而導致。他的血液中的戴奧辛含量高於政府認定的安全值一倍多。在審判過程中,密西西比州環保官員作證表示,該州的環保監測體制鬆散、環保官員常被大企業恐嚇壓制。一位由於鹽酸槽爆炸而受重傷的德立爾廠工人也作證表示,意外洩漏各種化學品的事件,在廠內屢見不鮮,各種危害化學品排放到環境中,很常發生。
在一審中,杜邦公司要求傳喚90幾位證人,但其中9人被法庭拒絕。杜邦以此為由上訴,說他們的證人被排除造成了不公平審判,也主張原告的很多證據與本案無關、可靠性低、對被告不公平,應該排除。案子最後到了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決:在排除大量原告的證據後,重啟陪審團審判。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狄雅茲(P. J. Diaz)和其他兩位大法官反對這個判決,指出:杜邦要求排除的證據,要不是其實對公司一方有利,就是可靠性與相關性都不低;其他大法官支持杜邦排除這些證據,非常不公平,而且,在他所參加審判的8件大企業被陪審團判決應給付小市民損害賠償的案件中,7件都被最高法院翻轉原判決,判大企業勝訴。
即使狄雅茲大法官批評得這麼嚴厲,密州法院還是在2007年把斯特朗案發回更審。在排除了原審所提出的大量證據後,更審的陪審團判決證據不足、杜邦勝訴,不用賠償。
台灣當前的政治社會體制,處理公害案件的模式與大量依靠司法訴訟的美國不盡相同。但是,如果密西西比州的集體癌症「疑案」發生在彰化,台灣的公民社會、各級政府、與法院的表現,會更有效嗎?大部分人的估計應該是:不會吧?
C8案與杜邦化工的消亡
雖然在密西西比州的二氧化鈦廠公害爭議中,杜邦在司法上贏了一次。但是,在北部俄亥俄與西維吉尼亞兩州交界處的俄亥俄河谷中游,另一場持續了十幾年的公害訴訟,卻使得杜邦公司真的連兩百年老店的招牌都真的砸掉了。
這個爭議的核心,是杜邦化學公司專利的鐵氟龍不沾鍋和3M公司的防水防污織品與紙類塗料「司高潔」(Scotchguard) 中所含有的全氟烷化物(PFCs)的問題。和許多化學品類似,杜邦在1938年推出鐵氟龍(Teflon,學名為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ylene,簡稱PTFE)時認為它是完全無害的。PFOA(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又名 C8,因為分子上有8個碳原子)和PFOS(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sulfonic acid)兩種長鏈的PFC是製造鐵氟龍的中間原料。[2]
1980年代,杜邦和3M在廠內體健時陸續發現員工血液中PFOA和PFOS的含量日漸增高,並且女工的孩子開始出現先天缺陷。到了1990年代,杜邦和3M觀察到鐵氟龍廠員工罹患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比例明顯增加。鐵氟龍有害健康的消息開始在媒體上愈來愈引人注目。但是公司一直否認有任何危害,把他們在廠內的研究發現保密。直到1990年代末,3M和杜邦才宣布將開始用短鏈的PFC來取代PFOA和PFOS,但還是否認這兩種物質有顯著的健康危害。
1999年,杜邦在西維吉尼亞州俄亥俄河中游生產C8的杜邦華盛頓廠附近的一位養牛的農民特儂(Wilbur Tennant),認為自己的牛是被杜邦的廢棄物毒死的。杜邦公司買了他的一塊農地,直接把含C8的工廠廢渣傾倒在農地上。顯然有不少化學物隨著溪水流到了牛喝的水源中。因緣巧合之下,特儂找到一位熟識的律師幫他打官司,向杜邦求償。根據美國的司法制度,民事訴訟的原告可以要求被告提供訴訟相關資料(稱為「事實揭露」, discovery)。特儂的律師提出告訴後,杜邦運了一卡車的影印資料給他:典型的大企業作風,欺負小律師事務所沒錢沒人,用資料淹死你。
就在原告律師耐心地翻閱一箱又一箱的資料時,杜邦總公司法務室的環境法律師萊利(Benard Reilley)在後來被訴訟程序揭露的一封 2000年8月的email 裡,對公司主管說:
西維吉尼亞州的這坨大便終於要打到電風扇了!那農民的律師終於搞懂了不沾鍋問題。他威脅說要向媒體公布,來抹黑我們,好跟我們勒索大筆和解金。操他娘!
諷刺的是,萊利本人在另一封 email 裡警告其他主管,訴訟中,任何文件都可能會被對方律師拿來當證據,所以寫 email 時千萬要小心。我們可以想像,15年後,當杜邦C8案真的開庭審理時,萊利律師的這些詞句在法庭被公開唸出來時,陪審團與在場媒體記者是什麼感覺。
杜邦在2001年與特儂就他的牛的問題達成和解,金額保密。但是,在特儂的訴訟的媒體報導中驚覺到C8問題居民與工人,從2000年初已經開始對杜邦提出集體訴訟,認為他們的生活環境裡的土壤地下水中所累積的C8已經造成健康危害。世界各地關於PFOS與PFOA的健康風險的研究開始比較大量出現。然而,在鐵氟龍危機中,發展出替代品並因而繼續獲利的,還是杜邦與3M兩家始作俑者。
2005年,俄亥俄河中游杜邦C8訴訟兩造在西維吉尼亞州地方法庭達成暫時協議,委託一個由三位知名公衛學者組成的C8科學委員會對案情做進一步的科學調查,兩造都不得干涉委員會的研究。經歷7年對於杜邦廠工人和周遭社區居民的研究、花費掉350萬美元,理應由杜邦公司支付、但聯邦環保署補助了不少的經費後,C8科學委員會的團隊終於發表了35篇同儕評審科學期刊論文,把C8的暴露與包括22種癌症在內的55種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建立起來。
該案在2015年9月在俄亥俄州的聯邦地區法庭開始審判。根據之前的協議,杜邦公司不得再就已發現的暴露與疾病之間的一般因果關係爭執。[3]這個不尋常的訴訟程序或許會成為未來毒物侵權訴訟的重要參考。另外,雖然鐵氟龍的危害可說是食安問題,至今全球每個消費者都可能受到PFOA和PFOS或多或少的暴露, 但是,能夠供流行病學調查的長期穩定受到暴露的人口,還是工人與在地居民,使得問題呈現為主要是職業病與環境污染議題。
更重要的是,雖然使用新的短鏈PFC製造的鐵氟龍進入市場以及常人生活環境中只有十幾年,科學界已經開始呼籲應該應該把包括長短鏈PFC在內的多氟與全氟烷基物質(poly- and 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視為同一群潛在的危害化學品來進行有系統的研究。2015年4月,國際上200多位科學家,包括一位台灣國衛院的流行病學家,聯名呼籲各界重視PFAS及其替代品的危害可能性。他們連署的《馬德里宣言》中的訴求就包括開發檢驗方法、登記彙整物料清單、進行化學品的「環境宿命」(environmental fate)調查以及進一步的毒理學和流行病學研究,以及發展從機器、法規、到科學的一整套因應措施。[4] 這或許會是加速人類社會辨識因應危害化學品的「生命週期」的一步。
2015年9月底開始的杜邦C8集體訴訟,聯邦地區法庭很快地在10月8日由陪審團判決必須賠償其西維吉尼亞州鐵氟龍廠鄰近的俄亥俄州一位女性居民 Carla Bartlette 160萬美元。陪審團判決,杜邦公司長年排放在俄亥俄河與其他水體中的鐵弗龍原料PFOA導致Barllette 罹患腎臟癌。[5]
這是近3500位居民對杜邦提出的集體訴訟中,由兩造同意選出的六件先導案例(bellwether case)的第一件,也是被告認為病情最輕、因果關係最不明確的一件。可以想見,之後的數千名受害者的賠償金額只會更高。杜邦在2016年初與受C8污染的4家地區自來水公司之一和解,金額保密。到了2016年7月,法庭正在審理第四件賠償案。[6]中間兩件還沒開庭就和解了。同時,杜邦的兩個海外鐵氟龍廠,正在受到日本與荷蘭當局的嚴厲檢視,周遭居民開始接受大規模血液篩檢。
由於C8訴訟和其他利空消息,杜邦股價從2015年3月到9月底直線下跌了將近38%,董事長兼執行長於當年10月5日下台。但是,更有遠見地,杜邦在2014年底已經開始籌劃把二氧化鈦、鐵氟龍、與冷媒[7]三個牽涉到鉅額訴訟賠償部門的37個廠、以及174個污染場址切割出去,成立一家「科慕企業」(Chemours),準備一旦官司敗訴定讞,就放給它破產,讓人求償無門。1990年設立在台灣桃園觀音的二氧化鈦廠也被切割到這家「科慕企業」。
這家公司在2015年6月上市,IPO股價被炒高之後,包括杜邦大股東在內的許多原始股東應該都出脫股票給散戶冤大頭了。華爾街分析師憤怒地控訴:杜邦公司在真實環境中散佈毒物,現在又要把這些「有毒資產」散播給投資大眾。[8]曾幾何時,化學的「毒」已經成為談股市時不可或缺的象徵了。
為了怕切割出去還不足以逃避賠償,杜邦於2015年12月又宣布與另一個巨型化工企業陶氏化學(Dow Chemicals)合併,並準備把兩家公司在3年內拆成三家。屆時,杜邦這塊招牌將會消失得了無蹤影。
反公害運動的挑戰:東亞道路的特色
1986年鹿港居民走上台北街頭時,一群老人手持黑底白字的「怨」字,是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最經典的畫面。第二年開始的後勁反五輕抗議也沿用。1990年代關廠工人抗爭時身穿黑布,上書大大的「怨」、「恨」。悲情、憤慨、無助、控訴,自此之後數十年,幾乎就是「抗議」的唯一主調。
2010年代,當1990年代的關廠工人群體被迫再一次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時,「怨」、「恨」的黑底白字又出現了。但是,這次還有個不那麼悲情的字:「幹」!經歷了十餘年的抗爭,以及運動中快速讓人看盡世間百態的經歷,這些資深抗議者其實已經早就超越了無助的悲情,而是有著自己群體不同於官商主流的價值觀,很大成分是為了原則問題而戰:政府這樣做是錯的,我們要糾正他!
在「怨」字畫面主導下的1986年,談論鹿港反杜邦問題的輿論,事後看來,充滿了豐沛的感情,但嚴重缺乏所謂「科學內容」:二氧化鈦廠的製程是什麼?主要可能的污染物是哪些?污染防制設施有哪些?效果如何?可能的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有哪些?我們已知的這些研究可靠度如何?其他不同的說法的可靠度又是如何?、、、等等。雖然報紙雜誌報導都有小方塊式的解釋與介紹,但是,在整個辯論中,這些問題都一直不是重點。
這不能怪「民眾沒有科學常識」,因為支持杜邦的論述也一樣「不科學」,一面斥責民眾「不理性」,一面非常不理性地說:像杜邦這樣的國際級大企業,必然會把污染防治措施作得很好:沒有論證、無須證據、訴諸權威,而且是一個到了2010年代被證明是無恥騙子的權威。
當年7月,中研院院長吳大猷,知名的物理學家(但是人們對他的物理研究似乎興趣不大),投書《民生報》反對杜邦設廠計畫,同樣沒有什麼「科學論述」,而是平易的政治批評:
這次反對二氧化鈦廠,筆者深信汙染祇是理由之一,在幾個「反對」事件間,都有一共同點,即人民對有關機構的不滿和失去信心,「反對」乃間接的發洩其不滿的一種表示形式而已。…
至組隊去美參觀杜邦廠鄰近環境之舉,則一大怪事也。杜邦完善的處理廢水廢物,自然可信;它絕不會有淡水河的情形,是既無需去參觀,即去看亦看不出什麼毛病的。即以美國三哩島言,在出事前一天,如我們組一隊人去參觀,又能看見甚麼嗎?「組隊去訪察」,是幼稚、或自己騙自己之舉。…
新竹有兩個工廠,附近居民不堪其廢氣等汙染,已數年了。年前似曾勒令其一度停工,但目前情形似又嚴重如昔。我們各類工廠,幾可以隨處建立;設廠前,它的防止汙染條件似無機構審核限制;設廠後,它的汙染,亦無機構執行解決問題的措施。總觀這些,和垃圾、河川水產各種汙染情形,我們實在不能怪人民對政府漸失信心的。(1986-07-11/民生報/03版)
耐人尋味的是,黑底白字的「怨」字,其實不是台灣獨創,而是從土本典昭等戰後日本著名左翼影像工作者對水俁病受害者的抗爭的紀錄片中看到的。戰後日本四大公害案:熊本水俁病案、四日市哮喘病案、新瀉水俁病案、富山縣痛痛病案,每一個都有「怨」字背後所凸顯的特質:悲情、無助、對政府沒信心又憤慨。
而當時的日本政府也當真不知如何應付,只能被動承受民眾的憤怒。對這些病症的「先進國家科學研究」都很少,而且日本的案例往往就是世界首例。發現並定義這些疾病的科學研究者,往往連在日本都屬於邊陲。首次提出有「水俁病」這回事的熊本大學醫學部的研究者,呼籲了好幾年都不太受重視,這跟他們不在東京、京都等核心地區的一流學府,恐怕脫不了關係。有些疾病,如鎘中毒造成的「痛痛病」,連命名都土味十足到令人心酸:罹病的農民躺在榻榻米上哀嚎「Itai, itai!」
「怨」字背後的感情,似乎是急速工業化的東亞各社會的一種共通的歷史經驗,在韓國也不少見。從日本明治維新開始,在追、趕的高速中建成的許多工廠、新開發的許多製程、排放出的許多罕為人知的廢棄物,造成了人們承受許多前人所不知的健康代價。但是,主持著這些飛速發展的科技官僚們,以及與他們共生的威權政府,又往往給人們帶來一種幻想:科學什麼都知道;政府裡的人懂科學;我國政府官員不懂的,「先進國家」(多半也就是美國)一定有「學者專家」懂…。這一成套的幻想如果成立的話,那麼,我們有問題,而政府不解決,一定是他們不願,而不是不能。
「怨」、「恨」、「幹」!
1986年的反杜邦群眾懷疑,當時的政府其實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幹什麼,事後看來是真的。
關於二氧化鈦的致癌風險、關於二氧化鈦廠排放的污染物的流佈與其環境影響和健康影響,以及當時環境問題中無數的具體科學問題,「先進國家」的研究也才剛開始。而且,在杜邦C8案揭發出來的案情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知識資訊在大企業的保密之下,都得經過無數人許多年的努力,才得以為人所知。科學面對浩瀚無邊的世界時的無知窘困,是有其社會背景的。東亞道路的特色,在於我們這種後進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官民上下共享的「對無知的無知」:我們不知道,有很多事情,其實以前沒人懂,我們或許是天下第一個懂的。
1986年的反杜邦群眾抗議所打造出來的當代史給我們的啟示,不僅僅是群眾有力量、民主可貴、環境需要捍衛、黑箱決策不可信、等等。這些在三十年來已經成為眾人共享的信念。如果要更進一步,我們必須接受、打造「對無知的認識」。「已知的無知」比「無知的無知」,總算是進了一步。
1986年的反杜邦群眾,有很多東西還不知道;1986年支持杜邦的政府官員,也有很多東西還不知道。2016年的我們,依然有太多需要知道的還不知道。
(原載於 范綱塏 採寫/編纂 《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紀錄文集》(台北:人間,2016),5-25頁))
[1] 成員包括台灣省環保局長莊進源等有關官員,彰化縣議會副議長謝式穀、鹿港鎮民代表大會主席葉萬崇、及國內主要新聞機構記者。
[2] 看到這裡,或許很多讀者會開始擔憂,自己廚房裡的鐵氟龍鍋是不是也會釋放出致癌物?
答案當然不會是確定的「會」或「不會」,而是某種機率。但是,這種機率顯示出化學品危害案件常見的,案情事實與大眾關注之間的典型隔閡。根據到目前為止各個機構的研究,消費者通過鐵氟龍、司高潔等產品所暴露到的C8或PFOS,相較於通過污染的飲水和工作現場暴露的工廠附近居民與工人所暴露的量,微乎其微。但是,人們對消費品毒性的憂慮,通常會遠高於對環境公害或職業安全衛生的關注。從而,食安問題會引起強烈的公眾反應,環境污染其次,職業病則更少公眾會關注。
[3] 關於毒物的訴訟,如職業病訴訟,爭執通常在兩個層次的因果關係上:「一般因果關係」指的是A物質有顯著的可能性會導致B疾病;「個別因果關係」是指原告所罹患的B疾病非常可能是由被告所排放或使用的A物質造成或促發的。
[4] Green Science Policy Institute, “The Madrid Statement on Poly- and 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 http://greensciencepolicy.org/madrid-statement/. 「環境宿命」又稱「環境流佈」,是研究一種污染物(典型來說是合成化學品)在生態環境中的散佈、轉化、循環,例如日本水俁病案例中,工廠排放水中的有機汞,最後進入人體、造成危害的路徑。
[5] Bartlett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Civil Action 2:13-md-2433, Case No. 2:13-CV-0170, Unite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Ohio, Eastern Division. October 8, 2015.
[6] 這第四件個案,一位罹患睪丸癌,但目前恢復良好的男性,於2016年7月7日─9日被陪審團盤決勝訴,杜邦應賠償他510萬美元健康損害,外加40萬美元懲罰性賠償。David Freeman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Civil Action 2:13-CV-1103, Unite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Ohio, Eastern Division.
[7] 杜邦專利的氟利昂(Freon)冷媒是20世紀中期用來做為冰箱冷氣冷媒和噴霧罐推進劑的氟氯碳化物(CFC)中產量最大的。1980年代CFC被認為是破壞臭氧層最重要的兇手。於1987年的蒙特婁公約中,各國同意逐步淘汰CFC。杜邦用其他碳氟化物來取代氟利昂中的CFC,但之後該物質又被認為是嚴重的溫室氣體而被1992年京都議定書相關協定要求逐步退場。
[8] Citron Research, “Chemours Is a Bankruptcy Waiting to Happen! Chemours Was Purposely Designed for Bankruptcy! This Stock Is a Zero,” Citron Research(2016), http://www.citronresearch.com/chemours-is-a-bankruptcy-waiting-to-happen-chemours-was-purposely-designed-for-bankruptcy/.

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紀錄文集
作者:范綱塏(主編)
出版社:人間
出版日期:2016/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