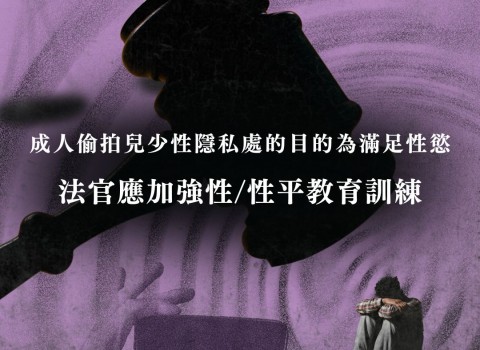文/李冠霈(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專員)
前言
自1997年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迄今屆滿20年。隨著2012年梁振英接任香港行政長官後,其加速推行港深兩地融合政策,更激化香港民眾對政府在經濟、政策、文化面向發展的不滿。2014年,分別在香港、台灣發生的雨傘運動與太陽花運動,各自展現兩地公民社會對於來自中國威權政治力的積極抵抗,同時帶出港、台公民運動中的對話。在香港,因雨傘運動遭逮捕的抗爭者伴侶,也因其入獄而被群眾擁簇出頭,成為新的鎂光燈焦點;然而,這些「伴侶」在整個運動歷程中,與入獄者同樣擁有運動者/抗爭者身分,在過去卻由於性別因素而隱身於公民運動中未被看見。
基此,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於10月29日在塩旅社舉辦一場「政治暴力下的親密戰友─港台民主運動中的女性經驗」座談會(下簡稱本座談會),邀請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何式凝教授、五名公民運動者、台灣作家胡淑雯及高雄醫學大學性別所李淑君助理教授一同對話。嘗試以性別視角觀看港、台灣的公民運動經驗差異與共鳴,以及身處威權政府下,公民運動者如何同時面對交織其身負對抗國家機器與父權社會的雙重枷鎖,並且展現其能動性。
因性別而隱身的運動主體
本座談會邀請的五位公民運動者皆為女性,年紀為二十至三十歲不等,屬於新生代社運人士。從她們現身說法可知,作為「女性」參與雨傘運動時,自身的運動主體容易在以男性為主的陽剛社運場域裡隱形;同時,具備男性運動者「伴侶」的身分,也使她們總是以「關係人」而非運動者的位置被群眾認識。參加座談的香港公民運動者袁嘉蔚表示,「我不只是羅冠聰的女朋友,我也是一名抗爭者,我出來(講話)不是因為我是羅冠聰的誰,是因為我是袁嘉蔚。我參與社會運動也有六年的時間,但在羅冠聰入獄期間,我被當成替代品,當他(從監獄)出來,我就退回專門聯絡員。」
高雄醫學大學李淑君助理教授指出,上述公民運動者因性別而被隱身的主體位置,此種對女性不平等的經歷,與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一群投身社運的女性雷同。過去這些台灣女性,也因為大眾對性別位置的刻板想像,在其同為抗爭者的丈夫被捕入獄後,被當時群眾期待該以政治犯配偶身分「頂替」丈夫們在獄中的「過渡時期」,完成服刑的丈夫在政治運動中的任務與功能;在伴侶出獄後,又期許她們該「回到」運動者伴侶的輔助位置,許榮淑、周清玉等人均屬之,她們的位置猶如戰爭時期後勤女工的角色。
本文認為,無論在先生/伴侶入獄時或出獄後,主流媒體對這群女性社運者的想像,始終停留在期待她們當個「好妻子」、「好女友」的關係性角色或替身上面;相較於她們,男性社會運動者卻鮮少面臨因性別而被隱身的處境。造成此現象的因素之中,無法忽略的是整體社會從未拔除因性別差異而存在「女性應做賢內助」、「男性較適合與體制衝撞的陽剛場域(如社運現場)」、「男性較能擔當領導位置」等刻板印象。
被性/別化的運動身體
另一方面,有別於二、三十年前,近年港、台參與社會運動的成員不再以男性佔絕對多數。惟,參加本座談會的香港公民運動者表示,當女性參與社會運動時,除不若男性容易打入領導群體或成為領導者外,其身體形象、容顏外貌、私領域生活也總是被擺在她們對該運動的主張之前。此種現象亦發生在台灣,如2014年太陽花學運中,被攝影師捕捉到容貌與身材符合主流男性凝視下女體形象的劉喬安,曾遭當時中天新聞台《新聞龍捲風》節目的評論員彭華幹以性化的字眼描述其胸前未拉拉鍊「超殺、超正」。對此,作家胡淑雯回饋表示,「現在你們(指參與本座談會五位公民運動者)面臨的是被狗仔化的對手、被庸俗化的群眾政治空間。你怎麼樣都不對,跟誰在一起不對、不跟誰在一起也不對,這時候正是時候發展出一種女性運動者的內聚力量,有些事情適合用自己的方式先處理。」
本文認為,女性運動者與男性運動者同樣面對國家機器與反對輿論,同時又承擔了父權凝視下異性戀單偶制「忠貞」標準的檢驗,或被擺在「關係人」的輔助位置而無視自己身為運動主體的訴求,或個人身體形象被侷限在主流男性凝視的女體單一想像窠臼中。是以,如何鬆動威權體制結合父權社會加諸這些女性身上「性/別化的身體」與「隱形的主體位置」,無疑是她們面對此雙重鞭笞的一大課題與挑戰。
結語
近年來,港、台公民運動中的性別比例已漸趨平衡,女性不再屬於運動中的絕對少數。然而,因性別而生的不平等更伸入運動位置與能見度向度,「如何被看見」、「被看見何種樣貌」等是女性運動者面臨政治與性別的交織命題。本文綜合本座談會來台交流的新生代運動者現身說法,以及過去台灣社運中的性別現象,從公民運動者的性別對其參與社運過程的影響,分為「被隱形的主體」與「被性/別化的身體」兩個議題進行討論。筆者透過本座談會看見,來台交流的五位香港公民運動者,嘗試藉由與台灣與談人、聽眾的對話交流,釐清自己身處的運動環境對性別平等存在何種更深層的匱乏內容,同時也內聚自身的女性力量與內涵,這正是她們面對因國家與性別因素,加諸身為女性公民運動者的雙重不利時,展現能動性的方式之一。